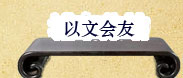内容
活着
活着 
我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南州北部山区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喜凤。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我随着我的父亲到我祖父家去避难。那年北风异常的凛冽,7月下旬,中国也迎来了少见的高强度“二度梅”,南北地区都相继出现了大面积的洪灾,受灾人口达到了上千万,中国大地随处都可以看见难民。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到我祖父所在的山区,而我与喜凤相识则完全是因为一场意外。
喜凤并不是我祖父那个小山村里的,或者说她与我一样都是避难者,不同的是她是流浪到我祖父所在的山区。那天是一个少见的晴天,东方那个名叫阿波罗的家伙终于撑着发白的肚皮,懒洋洋地出现在山里人的面前。我背着背篓,拿着弯镰,招呼了和我年龄相近的阿布到山上去割羊草。这是我到我祖父家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就是随着我的父亲学习文艺。阿布发现喜凤完全是一个意外,那天早上他吃了豆子,在山上割草的时候就不断的发出异响,后来他实在是憋不住了,提起裤子,青着张脸到山的另一山坳里去。而就是这个巧合让他看到了喜凤,现在想想,如果那一天我们不去割羊草,或者是阿布不吃豆子,或者他不到那个山头,他就不可能发现喜凤,也就没有我与喜凤的相识。阿布唤我的时候,我正在与一棵顽烈的碱草作斗争,听到唤声,我扔下手中的弯镰,不和这颗碱草一般见识,飞快的跑到阿布那里,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喜凤。当时喜凤头发很蓬乱,她的一双眸子凹陷,双唇干枯,脸色因为缺少营养显得很苍白,她的双手枯瘦,一只手拿着一个缺口的瓷碗,另一只手握着一根一头已经开裂的竹竿,她在地上瑟瑟的发抖。
阿布问我怎么办,我看着喜凤,当然,当时我还并不知道这个比我大十多岁的女子叫喜凤,我叫阿布到村里去唤大人。阿布像是一个领命的士兵,背着背篓,摇摇晃晃,飞快的爬上山,然后向山下跑去。不一会儿,阿布就领着一群人来到了这个山坳,领头的正是我的祖父,在我祖父的后面跟着的还有我父亲。父亲看了一眼就明白过来,这个女人和我们一样,都是“难民”。祖父下令,叫秋根叔背着这个女人下山,说不管怎样这是命,既然老天爷将她送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要尽天事,违背老天是要挨雷劈的。秋根叔是我父亲的兄弟,十三年前我父亲到县城里去,也在那个时候遇到了我的母亲黄桂莲,而我父亲的兄弟秋根为了照顾我的祖父留在了山区。秋根叔遵从祖父的命令,他俯下身子,然后我的父亲将喜凤扶在秋根叔的背上。秋根背着喜凤,他就像是一阵风,他没有花多少力气就将喜凤背回了家。在此后的多年,秋根叔给我说喜凤当时很轻,就像是鸿毛,一阵风都能够将喜凤刮起。
喜凤躺在祖父的床板上昏迷了一天一夜,她是在第二天傍晚时醒来的,当时我的祖父正在和我的父亲商量喜凤的未来。我的父亲说喜凤醒来之后就问她的父母在哪里,让她的父母将她接回去。我的祖父问,那他没有父母呢?父亲说,没父母她也要离开,一个大活人难不成还会饿死?我的父亲,也就是后来极力反对喜凤离开的那个男人,完全没有想到如果不是我们,喜凤还真的会饿死。我的祖父叹了一口气,他的神色显得有些凄然,他说,你们两兄弟都是一个妈生的,你的娃已经能够看羊了,而你的大哥秋根……这些年都是秋根在照顾我,如果可以的话,这女娃就留在这做秋根的女人。我的父亲听到这话,深深的抽了一口烟,烟头在黑夜里发出明亮的光,他说,那好,就做大哥的女人。
喜凤的第一次命运就在我的父亲将尼古丁吸进肺中的同时决定了。
我给喜凤做了一碗豆花汤,白白的豆花里放了些葱花,那些绿油油的葱花顺着白白的豆腐滚进了喜凤的口中,然后再顺势而下滚进了喜凤的胃里。喜凤睁开眼,她看到我将葱花顺着白白的豆腐送进她的口中,她睁大着双眼,硕大的眼睛瞪着我。我也用我的眼睛盯着她,我们大眼瞪小眼,然后我大叫一声,对着正在屋外商量喜凤未来的两个男人喊道,“她醒了!”
父亲将手中的烟蒂扔掉,随着我的叫喊,他和我的祖父两人踏进屋里,他问喜凤叫什么名字。喜凤睁着双眼,她瞪大着双眼就像盯着我一样盯着我的父亲。她脸上毫无表情,盯着父亲就像是在看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的父亲皱了皱眉头,再次问喜凤叫什么名字。喜凤还是睁着双眼盯着我的父亲,她不说话,也不笑,她就像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的祖父进来后没有说话,他打量着他未来的儿媳,就像是在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看到喜凤没有说话,他的眉头皱得比我的父亲还要深,心想喜凤不会是个傻子吧!
很快,整个小山村都知道了喜凤是个傻子,这个消息从村子的东边传到村子的西边,然后又像是一阵风刮到村子的北边,又送到南边。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救回来一个傻子,一个女傻子。阿布见着我就说那天我们救回来一个傻子,那个傻子什么话都不能说,她就像活死人,每天坐在门槛上一句话都不说。阿布来到我家,问门槛上的喜凤叫什么名字。喜凤扯了扯嘴,硕大的双眼盯着阿布,一句话也不说。阿布苦着一张脸,他说我们真的救回来了一个傻子。村里的人都来看我们家的傻子,他们他们见着喜凤就问她叫什么名字,见着我就问我们家是不是有个傻子。我说只好说是,而喜凤什么话都不说。喜凤是个傻子,秋根叔问喜凤叫什么名字,喜凤盯着双眼看着秋根,她这次扯了扯嘴角,她就像是知道是站在她面前这个男人将她背回来的,她说她叫喜凤。秋根叔笑了,他说喜凤不傻,喜凤叫做喜凤。
喜凤叫做喜凤,是秋根问出来的。我的父亲叫他大哥继续问喜凤是哪里的人,喜凤的父母在哪里。喜凤看着秋根叔,她嘴里就只知道说她叫喜凤,她说不出来她是哪里人,她的父母是谁。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叹了一口气,他们说喜凤就是一个傻子。然后他们再次蹲在院子里,他们又开始探讨喜凤的未来,他们要第二次宣读喜凤的命运。我的祖父说喜凤是一个傻子,傻子是不能够做秋根的女人的,傻子生出来的娃也是傻子,家里不能够再多出一个傻子,应该赶紧找到喜凤的父母,让喜凤的父母将喜凤接回去。我的父亲摇了摇头,他觉得喜凤的父母找不找得到还不好说,但是一个傻子不能够自力更生这是肯定的。我的父亲要将喜凤留下,他说不管怎样喜凤都是一个人,我们不能够看着一个人就这样死去,这是要挨雷劈的。我的祖父叹了叹气,他说那行,等找到喜凤的父母再将她送走。
喜凤的第二次命运在我祖父的一声叹息的同时决定了。
喜凤留在了我们家。她没有再坐在门槛上,她跟着秋根叔,我秋根叔走哪里,她也就走哪里,她似乎认定了这个背着她回来的男人。秋根叔到山上割羊草,她跟着;秋根叔到麦田里割麦子,她跟着;秋根叔去拾狗屎,她跟着……她就像秋根叔的跟屁虫,她什么都不思考,别人问她是谁,她还是什么都不说,她只对秋根叔说她叫喜凤。秋根叔看着喜凤,他说喜凤就像是盛开的花朵,越来越盛。
秋根叔是咧着嘴跟祖父说他要娶喜凤,他说他已经四十了,他要有个自己的女人。祖父瞪着他,祖父说喜凤是个傻子,说秋根叔娶了傻子,生出来的娃也是傻子。秋根叔不应,他叫我父亲去给祖父说。我的父亲说秋根叔已经四十了,如果再不找女人,就没有机会了,他说人不是古董,越放越有价值,人就是一块肉,放得越久就越容易腐烂。我的祖父没有答应,他说就是腐烂也不能够生出一个傻子来,不然就都腐烂了。我的父亲告诉祖父,他说傻子生出来的孩子也不一定就是傻子,傻子也能够生出聪明的娃,秋根很聪明,生下来的娃肯定随秋根。我的祖父咧嘴笑了,他肯定地说秋根随他,所以秋根才聪明,秋根和喜凤生下来的娃也一定随秋根,不傻。
喜凤的第三次命运就在我的祖父盼望孙子的同时决定了。
喜凤和秋根叔结婚的那天,我和阿布跟在喜凤的后面。阿布张着嘴喊着,阿布说花喜鹊,站树杈, 开口叫,喳喳叫: “要嫁人, 绣花针,花衣线, 绣个大红喜字入洞房。”那天人很多,村里的人都来看秋根叔和一个傻子结婚,他们在我祖父家里吃喜饭。我的父亲将喜糖扔在地上,我和阿布钻在村里大人的裤裆下,我们抢了很多的喜糖和豆子,那天我们吃了很多的喜糖和豆子。阿布的肚子被撑得像个超大皮球,他打着隔,他说他以后还要看秋根叔和傻子结婚,那时他要吃更多的豆子和喜糖。
喜凤成了秋根叔的女人,喜凤每天都跟着秋根,她和秋根一起去割羊草,她和秋根一起去割麦子,她和秋根一起去拾狗屎,她和秋根一起灌菜择菜……喜凤一天天地更加精神,她的笑容多了,村里的人看着喜凤都说,喜凤跟着秋根人都变聪明了,他们还都说喜凤不傻,秋根捡到一个好女人。
1998年洪水退去,我随着父亲回到南州县城。此后的每年春节我都跟着父亲回到北部山区去看我的祖父,那时秋根 叔总是会把我拉到旁边,他告诉我喜凤不傻,喜凤一直都不傻。我看着旁边穿着大红衣的喜凤,我也笑了,我说:“喜凤不傻,她一直都不傻。”
喜凤成了秋根叔的女人,村里的人都道喜凤不是傻子,可喜凤究竟是不是傻子最开始不是秋根叔告诉我的,而是喜凤她亲自告诉我的。
2000年,我已经上了中学, 寒冬腊月,呼啸的北风如同凶猛的野兽席卷了整个南州,我就是在大雪纷纷下回到乡下的。我的祖父已经年过花甲,他走起路来就像是跛脚的驴子,他不得不依靠着拐棍来支撑着他那只跛脚。我来到村口的时候,我的祖父也就用拐棍支撑着他那只跛脚,他看见我和我的父亲,他就咧开了嘴露出发黄的牙齿,他说你们来了。
我是在祖父家外的大松树下见着喜凤的,蓬松的雪花像玉屑儿似的,喜凤还是穿着大红衣服,她的肚子已经开始慢慢的长大了,她咧开嘴,她说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她说如果当初不是我与阿布发现了她,她就不会遇见秋根,也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很好奇,我问她为什么最开始她不说话,沉默的就像是一个傻子。喜凤露出洁白的牙齿,她笑了笑,那一瞬间雪花飘落,仿佛是跳舞的天使。她就在这里,用着近乎平静的话给我讲诉了一段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故事。
我出生在与南州毗邻的北州南部,我的祖父的祖父曾在清政府当差,我祖父的父亲也曾在国民党做过官,而我的祖父则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地主。我的祖父叫做刘三思,刘三思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富贵,以他的说法是要我的父亲将家里的富油给传下去。可是我的祖父还没有盼望着他的儿子将富贵传下去,他的家产就被几个挂红袖章的给抬走了。我的父亲给我说过,我祖父当初是活活气死的。挂红袖章的把他的桌子抬走,他就要抽搐一下;挂红袖章的把红床抬走,他就要抽搐两下;挂红袖章的把他的金匣子抬走,他就抽搐三下……我的父亲给我说,我的祖父就是在挂红袖章抬东西的时候,一下两下的抽搐死的。我的祖父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了一笔丰厚的家资,他有二十多亩地和八头牛,他还雇佣了几个佣人。可是我的父亲不仅没有从我的祖父那里继承这笔家资,而且还把应该戴在我祖父头上的资产阶级大帽子戴在了自己的头上。我的父亲那时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他没有像别的红卫兵去捉人,他要替自己的父亲到广场去挨批斗,说好听一点是批斗,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挨骂挨揍。本来应该是我父亲的家资被红卫兵拿去分了,所以我的父亲当时是一贫如洗,更是因为做了我祖父的“替死鬼”,直到文革结束村里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
我的父亲和我母亲是在文革结束一年后才相识的,那时我的父亲才三十岁,但是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就像是冬雪里掉在屋檐下的冰凌,雪白得就像玉屑儿。我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是靠卖煤球的那点利差维持生计,他每天将煤球从东村卖到西村,再由西村卖到隔壁的东村,就这样他就越卖越远,他遇到的人也越来越多,一直到他遇见我的母亲王淑慧。我的母亲王淑慧在我父亲之前还有一个男人,她给那个男人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就在生下儿子不久,王淑慧的男人因为做工回家喝了一口凉水给害病死了。王淑慧就一直孤苦的养着她的儿子,也就是我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平日里也没少遭到白眼,乡里乡亲的都说她是一个克夫命,要不然怎么会喝口凉水就把人喝死。我的兄弟比他的父亲更短命,他六岁那年王淑慧给他做了些豆子,可是没有想到他吃着豆子竟然给撑死了。王淑慧生命里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喝凉水喝死,另一个却是吃豆子撑死。别人都说我的母亲王淑慧是一个克命的女人,她不仅要克死自己的男人,也要克死自己的儿子。
我的父亲富贵与我的母亲王淑慧是在田埂上遇到的,那天我的父亲挑着煤球,他卖了一天,从太阳出来卖到太阳天落下去才买了一半,他就挑着这一半煤球与他的女人相遇。王淑慧叫住他说你是卖煤球的,你给我挑二十个,行吗?我的母亲对着他面前的男人说“行吗?”,好像这个男人会拒绝他似的,她要征求这个男人的意见。我的父亲说当然行。我的父亲理所当然的将煤球挑到王淑慧的屋里,他帮王淑慧把煤球放好,然后又将王淑慧墙角的水泥砖码到另一个墙角,最后他又将王淑慧陈年的谷子搬出来晒……王淑慧对我的父亲说谢谢。我的父亲咧开了嘴,露出了他洁白的牙齿,他说他是隔壁村的,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站在田埂上喊一声他就知道了。王淑慧不好意思,但是她还是应了。就这样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越走越近,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不挑煤球了,他把王淑慧挑回了家。两个不幸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他们就像是大河中的玻璃瓶,无论怎么飘荡,总有一天要上岸的。我的父亲与我母亲在一起,生活并不是很好,我的父亲不挑煤球了,他帮别人做一些重活,这个本来应该像地主一样活着被仆人伺候的男人却做起了比仆人更低贱的活,他每天都要看别人的脸色。有的脸色红,有的脸色青,有的脸色白,有的脸色黑,我的父亲知道哪些脸能够得罪,哪些脸不能够招惹,哪些脸又是和善,遇到红脸他就知道遇到了好人,遇到青脸和黑脸他就知道自己遇到了惹不起的主,遇到白脸他就知道这个人反复无常。我的母亲则是在家里帮着做一些手工活,每个月能够赚两三个小钱补贴家用。我的父亲与母亲小心翼翼的维持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家,他们把它视若珍宝,小心的经营,不让它受到丝毫的伤害。
我是在我母亲成为父亲女人的一年后出生的,那一年的雪下得很大,老天爷就像是喝醉了酒,发着酒疯,一股儿把积占一年的气全撒在了那一年的冬天。我的母亲憋足了气,那一口气直到我发出响亮的哭声,她才咽下去,在她咽气的时候她仿佛听到了远边喜鹊的叫声,叫得那么凄惨。这一次,我的母亲没有克死她的男人,她给她的男人生了一个女儿,他的男人给她的女儿取名叫做喜凤,也就是我。我是喜鹊,就是我的叫声将我的母亲叫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的母亲咽气后,我的父亲又要当爹,又要当妈。我的父亲给别人挑粪,他每天早上起得比太阳还要早,他每天晚上睡得比月亮还要晚,他把应该在襁褓中的我背在背上,我就每天闻着粪的臭味和我父亲的汗水味一天一天的长大。在我十岁那年,我的父亲全身无力,他走起路来最开始是一软一软的,再后来他连一软一软走路的资格都没有了,他每天都只能够躺在床上,他望着茅草屋屋顶,两眼无光,他对我说喜凤,我死了你可咋办啊?我当时笑,咧开的嘴,就像王淑慧对她的两个男人咧开嘴一样,我说爸爸,你不会死的,我一定会把你救活的。我们一家的担子最开始是由母亲和父亲一起挑着,然后由父亲一个人挑着,最后只能够落在我的肩膀上,虽然我们很苦,但是我们一家三人毫无例外的对命运做出了最顽强的斗争。我十岁就开始做工了,别的小孩还依偎在父母的怀抱,我已经学会了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的赚一些小钱,虽然勉强支撑着自己的生活,可是我父亲的病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恶化。父亲开始挑粪的时候时常感到身体发软,然后是走不起路只能够躺在床上,然后他每天的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最后他的眼皮和嘴都张不开了,直到有一天他将一口空气吸了进去就没有力再吐出来。我的母亲离开了我到白白的云朵上去了,我的父亲终于耐不住寂寞到白白的云朵上去找我的母亲,只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流浪,我记得那年我十一岁。
十一岁的我还能够靠着缝缝补补活下去,可是命运不济,在我十九岁的时候闹饥荒。平日里还有富裕家的人叫我给他们缝补点东西,可这一闹饥荒自己就过不下去,谁还会让我缝补啊。我一个人,又没有什么家当,除了每天吃点陈本维持着生计,就几乎没有什么收入。靠着乡里乡亲的施舍,好不容易维持到来年春季,可是没过多久闹起了洪水,所种的粮食一股脑儿全部被洪水给偷着吃了。我开始流浪,我从那里流浪到这里,在遇到你们之前我已经八天没有吃东西了,别人都说七天没吃东西就要去见地藏菩萨,可是我坚持了八天,不过我也知道我不可能会坚持到第九天,还好我遇见了你们,否则的话我也没有机会坐在这里给你讲故事了。
雪越来越大,这就像老天爷在向谁发着脾气,一个喷嚏打下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打到“被窝”里去藏着。远处的房檐已经挂起了冰棱,尖尖的冰凌照射着玉屑儿似的白雪,晶莹剔透。我问喜凤,为什么你在醒来之后还不愿意说话?就像一个傻子。
喜凤捋了捋她乌黑的头发,在白雪中熠熠生辉的头发,她说,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活下去,我生下来把我的母亲叫到了地狱,然后我拖累着我的父亲直到我父亲患了没有力的病,最后我又一个人活着。每一天我都与老天作斗争,一天两天三天,我坚持了八天,直到遇见了你们,然后我又成了秋根的女人。我才明白,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为自己,为别人,静静地活着。
那年的雪很大很大,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喜凤出生的时刻,老天将积攒了一年的气全部灌进每一个人拉拢的大皮袄之中,每一个人都哆嗦在被窝里不敢伸出头来。喜凤的笑容在冰雪里像一朵花儿绽放。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发表评论


分享本站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4 小路(三十 )
- 浏览:53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2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8 樱花树下
- 浏览:48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2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322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90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4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9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4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5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57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6 换妻
- 浏览:16248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