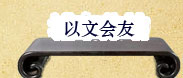短信与爱情 
小芳的习惯是午休时间上网阅读。如今,她跟许多人一样,浏览、看新闻都在网上。她正在看一段“屁评”,手机短信铃声响了一下,她没有理睬,继续着正在做的事。如今短信满天飞,理它干吗?上班时间到了。小芳退出了浏览的网页,伸了个懒腰,闭上眼睛,脑子里快速理了一下下午该做的事,习惯性地拿出手机扫了一眼刚才那条短信,其内容是这样的:我再一次问候你,近来可好?难道你连我是谁都不想知道吗?自:“Z”“Z”是她给一个“神秘”的手机号起的“名”。那还是上半年“五。一”节左右的时候,她收到了第一条来自这个“Z”的短信,内容是她年轻时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改编的:问候你朋友,桃花又开透,……
匆匆的时光如梭,
岁月如流,
淡淡的回忆如梦,
往日不回头,
曾经的甜蜜,
今又上心头,
……
后面几句很缠绵,一首典型的新体爱情诗!她笑了一下,看了一眼来信的手机号:不认识。跟处理许多垃圾短信一样,删除完事。
时隔不久,她又收到了这么一条情切切、意绵绵的短信,发现来信手机号与上次那个手机号很像,也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删除之前,鬼使神差,提取并保留了号码,还取名“Z”。
又过了些日子,这个“Z”又来了一条内容近似的短信,仍然是情切切,意绵绵。当时她想到电话打过去问一下对方是谁?但又想到如今传说的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诸如某某手机响了几声不响了,打过去想问下咋回事?对方接了电话不吭声就挂掉了,可卡上的多少钱却不见了等等。类似的传闻还有很多。因而回问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照旧删除了事。
在小芳看来,被骗的绝大多数都是些心怀非分之想的人。不过这已经是三四个月以前的事了。她已经忘记了手机里还有个“Z”这回事。离异、且早过了不惑之年的小芳,对这种言情短信没有多少兴趣,远不像那些多情的男男女女偶尔收到一条“花信”,就满脸绯红,半天想入非非。只是从同一个号码多次发出,这种情况,她还是第一次碰到。而且就今天这条短信看,… …回复一下又有何妨?想到这,她先拨通了查询台确定了一下手机的当前费用,然后发出了回复:请问阁下是哪路神仙?好玄耶。
过了几分钟,她又拨通了查询台的电话,核实了一下刚才那条短信的费用:普通短信,就收了一毛钱。这一下,她心想: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是诈骗,但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被骗。
晚饭后,“Z”的短信又发了过了,这一次,她脸红了,心也跳了:
亲爱的:我不是什么神仙,我是个七情六欲一样也不少的俗人。要说神仙,你 才是我的神仙。在当年,你嘻嘻一笑,整的我神魂颠倒……嗨,不说了,本想现在告诉你我是谁的,但想到这半年多来你的冷漠,你还是先猜猜吧。祝好!自:“Z”。“Z”会是谁呢?
平心而论,小芳处世算得上低调、恬淡了,她几乎不跟人开玩笑。当然,这不妨碍别人开玩笑时她在一边无声的赔着笑。她的同事是不会有人跟她开这种玩笑的。难道是前夫?不会,缘尽缘散,何必?
从语气上看,对方应该是她以前的故知,而且还有那么一丝居高临下的滋味儿。到底是谁呢?她还想继续猜测推理,结果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根本就等于零。就在这时,有个影子在她脑海中一闪:不会是他吧?但她马上就否定了:不会,怎么会呢?
第二天星期二,上班时在处理案头事务的间隙,偶尔她还在做着这种猜测否定。
晚饭后坐下来看电视,猛的转念一想:也许是对方记错了手机号,把本该发给自己女朋友的短信发给了自己;也许是对方女朋友的手机号跟自己的很接近……对,肯定是这种情况。
星期三中午,小芳把自己推理的结论写成短信发给了“Z”:先生很可能记错了手机号码,发错了对象。之所以收到短信后“冷漠”,是因为考虑到自己是位又老又丑又胖的老太太。而先生的短信都是言情的。望先生查证为好。这条短信对自己老、丑、胖的描述,显然是夸张了一点。据说佛家劝说那些易犯色戒的信徒时说:当你们受到女色的诱惑时,就去想像她们衰老时的样子。佛家的理论是充满了智慧的。她之所以向一个未知的、甚至还不排除是恶作剧的人如此描述自己,可能是受了这种智慧的启发。
奇怪的是,信息发出后她并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静下心来,似乎心底里还有那么一丝企盼,盼什么呢?难道是盼“Z”的回信?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怦然心动呢?
星期三过去了,星期四又过去了。到了星期五的下午,她开始嘲笑自己:简直就是荒唐,几条没头没尾没来由的短信,竟然搅得几天神心不宁……唉,真可怜。由嘲笑自己到鄙视、再到怜悯,小芳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她想起了一个笑话,于是拿出手机写道:
隐形先生:周末了,送你一个笑话,笑不笑由你——大象把大便排到了路中央,恰好一只蚂蚁路过,它望着那云雾缭绕的顶峰,不禁感叹道:呀—啦—嗦,这就是——青——藏——高——原!她给“Z”发这个笑话,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这几天她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的,把小青年儿们的几条言情信息与自己这位中年妇女愣要联系在一起,实在是荒唐得有点离谱。
不曾想几分钟后,“Z”居然回信了:谢谢你的笑话。我今天很开心,也希望你开心。再见!
看到“再见”两字,不知怎么的,她心里感到了一丝空落。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再见”不是自己希望的吗?许多青年男女谈朋友最后告吹时,都是用“再见”收的尾。她想。与三天前相比,她已经基本恢复到了过去那个低调、恬淡的状态。不“再见”,难道还真的怦然心动不成?
晚饭后,她刚刚洗涮收拾清楚,想坐下来看会儿电视,短信铃声又响了。这几天,她对短信特别地敏感了起来。赶快拿过来看,只见写道:
想你,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见你,成了近日的期盼;
爱你,是我现在的追求;
梦你,是我曾经的情怀。
祝 周末好!
自:“Z”
哎哟我的妈,错了,绝对错了。都多大年纪了?还什么爱你梦你的,分明是毛头小伙子追女孩子的口气嘛。于是她迅速地写好了回信:隐形先生,这玩笑开大了!您肯定搞错了!这个号码的主人我确实是位年近半百的老女人。看你用情良苦且专一,可别误了您的正事。无意间我做了把那只“呀啦嗦”的蚂蚁,一笑了之吧。祝你好运!
发出后,她感叹道: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怎么就沾上了这等怪事?!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深圳卫视的“直播港澳台”开始了,这是她每天必看的栏目。此时,那位特约评论员刘和平正在用他富有个性的语言,犀利且入木三分地评说着当天的热门话题。短信铃声又响了起来,她再也听不进去那平日里令她啧啧赞叹、引人入胜的精彩评论了。“呼”的一下站起来,走进卧室,抓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了短信,只见写到:实在想不出该怎么称呼你,就叫你“丑老太”吧。别介意,只是个称呼而已。当年骄傲的你,随着岁月的流逝,竟变得如此自卑,令我很是意外。什么“丑老太”“老女人”?干吗如此作贱自己?你不老,我也不老,我们正当年!我不认为谈情说爱是青年人的专利。人本来就是感情动物。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让年龄左右?如果说青年人的爱情是季节催生的花蕾,那么如你我这样也算是经历了些世事沧桑的中年人,一旦萌生出爱情,那便是阅历精酿的美酒。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去,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公园戏班的演出现场,我邂逅了令尊大人推着轮椅上的令母看演出。你无法想象那个画面在我内心引起的震撼。试想:阳光下一对年近八旬的老人,老翁推着轮椅上的老妪,慈祥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幸福的笑容,欣赏着传统戏曲。那是怎样的情景,又是怎样的一种爱情?而这对老人的小女儿,却是我心头的那颗朱砂痣。要说老,那是以后的事。我要让你陪着我,我们一起去一天天变老。我没有搞错,你就是我当年倾心、这些年来一直不曾淡忘、如今仍魂牵梦萦的“芳”,好了,下星期天去看你。张!自“Z”
看完后,腾一下,一股热血直冲脑际,心也咚咚一阵狂跳,她赶快关掉了手机,她怕再听到短信铃声。是他,肯定是他!她再也无心看什么电视节目了。索性关了电视,倒了杯水端着进了卧室。
孩子晚饭后进了自己的房间。高三了,这孩子学习倒不怎么让人操心。她放下杯子又出来敲了敲孩子的房门,然后开门进去了。见孩子要做的作业,零乱的堆在桌子上,身子却靠在椅子上抱着本小说看。小芳知道孩子最近在看《宿主》。孩子见她进来只抬头冲她笑了一下,仍然低头继续看她的小说。她翻了翻那堆作业,都是一些模拟的高考试卷之类,便说:“这些作业,不做也罢。早点睡吧。”孩子又抬起头来,对她说:“你忙你的,你不用管我,到时候我收拾收拾就睡了。”自从上了高三,这孩子便再也没有周末了。
接下去,她开始慢悠悠地刷牙、洗脸、洗脚。想早点休息了。平时上床后,总要习惯性地翻几页书,她的经验是:这样有助于睡眠。可今夜,书拿在手里,思绪却怎么也集中不到书页上。张?难道真的是他?大张?一个高个头、腰板挺直、人称 “大张”的小伙的影子,在她脑海一闪,那是他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小伙脸膛黑红,厚嘴唇,一对小眼睛有事没事好眨巴几下。是她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芳发现他那对小眼睛眨巴起来特别滑稽,无意间四目相对,他就冲她眨眼睛,她忍不住就嘻嘻一阵笑。后来这一眨一笑几乎成了他和她之间的条件反射。他瞅别人的时候未必就眨眼睛,或者说他冲别人眨眼睛,别人未必就会笑。但小芳不行,她忍不住。即使到了二十多年后的现在,想起他那个滑稽相,她还是想笑。可她那个时候却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之间除了同学关系之外,还能有别的事发生?
可造化就是会捉弄人,他和她之间还真的发生了一段令人今天想起来,都感到尴尬不已的事。高中毕业,大张顺利地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候,高考一条龙。小芳却没能够得上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落入了中专。小芳上班两年后,大张毕业被分配到了市里一家机械厂。
那年中秋节,小芳、大张还有几位以前在另外同一个城市、后经考取不同院校、但各自毕业后,又被分配在这同一个城市的同学,在兰山顶上聚会。傍晚,他们站在山顶边聊天边等待月亮升起后拍照留念。大张和另一位同学在谈论围棋。都知道,大张的围棋很棒。此时他正在遗憾:今天忘了带围棋上山了,不然,现在就可以杀一盘了。
小芳望着山下渐渐被暮霭笼罩的城市,安静地说:“你们看,城市是不是就是一个棋盘呢?而你我所在的单位又何尝不是人家在这个棋盘上划定的一个个格子?”
小芳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她继续说:“我们大家像不像人家手里捏把着的一粒粒白的黑的棋子,然后按照他们的路数把我们摁进一个个方格里,我们就在那格子里成长、或者消磨、销蚀,直到终老、死去。这就是传说中美丽的‘优越性’。”
“不”,大张闷声说,“那是过去的事。你说的是我们父辈的命运……”
“说到父辈的命运,我还得唠叨几句”,小芳打断大张的话继续说:“在我们的父辈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年青、热血的时候,那可是,他们有思想,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们有文化,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文字;他们有技能,不能为社会同时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的语言、行为、吃什么、吃多少、穿什么、住在哪等等,都由别人给他们强行规定且不得违抗。别人让他们喊打倒谁,他们就得喊打倒谁;哪怕被打倒的,是他们崇拜的英雄、将军甚至导师;别人让他们去批斗谁,他们就得去批斗谁,那怕被批斗的对象是他们的至亲至爱至友。因为他们如果不去批斗,人家就会将他们拉过去一起批斗。还有,父辈的祖辈们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掳走还不算,那些财富同时还成了父辈和他们的祖辈们共同的罪恶……”小芳说着就有点激动了。
“可现在不是了”,大张抬高了声音打断小芳的话说。他有点听不下去了。
“现在改革了,如果‘格子’容许我成长,我就在‘格子’里成长;如果我只能在‘格子’消麽销蚀,那就对不起了!”
另一位同学说:“我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跟‘格子’往一块儿联想过。说真的,要不是我老娘前一阵动手术,现在我已经在深圳了。等过会儿月亮上来了,没准我在那儿吟‘床前明月光’呢。”
“对不起了?你还能怎么样?你能,你还上天呢?”说这话的同学是惠,惠是小芳的好朋友,大张的母亲是惠的姑妈,所以惠给大张说话,总带着点姐姐训斥弟弟的口气。惠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市里一家医院,她很知足。
“天是上不了的,但我不会向我老爹那样过一辈子的。咱们走着瞧。”说着,他又冲小芳眨了眨眼睛,小芳无声的笑了。
那次聚会后不久,大张给小芳写过一封很长的信,她也回了信。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其大意今天还清晰地记得。
大张在信中说:在哈工大时,他先后两次参加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考试,两次成绩都不错,但就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成行。现在被分配到了这家机械厂,他会利用一切可能想办法走出去的。
问小芳是否愿意同他一道离开这里,别再做那“格子”里消磨销蚀的棋子,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寻找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生活?还有,就兰山顶上小芳所说的那些话,他敢断定:这里不是供她成长的土壤,如果不离开,被消磨销蚀是注定了的……
大张的信写得很诚恳,可小芳总觉得有点玄乎。尽管当时出国热席卷全国,但小芳心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在给大张的回信中小芳写道:实在抱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我却深恋着脚下这片虽然贫瘠、但却不乏魅力的土地。你也许忘记了,当初我之所以放弃了别的选择进了中专,就是为了见识中国式的工业文明。这话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我是经过了一番挣扎的。至今仍不改初衷……我真诚地祝你在精彩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和空间!……
如果大张接到这封信后就此止步,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份怎么也挥之不去的尴尬了。
此后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月吧,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小芳正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上看一本书,书名到现在还记得,叫做《山坳上的中国》。就听有人敲门,拉开门一看,是大张。小芳愣了一下:“是你!?”
“怎么?不欢迎吗?”大张底气十足的说。边说边走过去自己坐到了小芳的床沿上。当时床上很乱。此时的小芳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一副邋遢相。一时难堪极了。便带有几分埋怨地说:“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大张却居高临下,理直气壮地说:“看你还需要打招呼吗?”
她听了这话,心里很有些不快,但还是很快地整了整衣着,梳了梳头。她洗了个手说:“给你倒点水喝吧。”可她拎起热水瓶时,却发现是空的,就说:“哎呀,没水了,你先坐,我去打壶水去。”到了水房门口的时候,她却向右手一拐进了厂工会的图书阅览室,从杂志架上取了一本《中国青年》看了起来。星期天阅览室全天开门。她是有意要凉一凉大张。他那说话的口气,实在让人受不了。
她看看表,半个小时过去了,这才慢悠悠地去开水房提开水。进了宿舍,大张说:“你总算来了。”她淡淡地一笑说:“下楼碰到了个熟人,多聊了几句。”她要给他沏茶,他从她手里接过了杯子说:“不劳驾你了。我外面还有点事,过来就是想看看你。现在好了,打搅你了。”说完他站起来,挺直腰板伸了个懒腰。小芳感叹了一声:你好高呀!他偏过头来,冲她笑了一下说:是高了一点,不过还不到一米八五。小芳要送他下楼,但到了楼梯口,又是那种口气:“请留步!”不容置疑。小芳站住了。这一次他没有再回过头来冲小芳眨眼睛。大张,确实是大张,现实、敏感且自尊。这一走,便再也没了音讯。直到第二年国庆节他结婚。
后来小芳意识到自己那天的失礼,给大张打过几次电话。那时候手机还未普及,电话只能打到单位上。可接电话的人总说大张不在。一次、两次,有了第三次,小芳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大张结婚的消息是惠带给小芳的。那天惠打来电话,说大张国庆节结婚,请小芳参加婚礼。婚礼上,小芳从惠那里知道了大张的新娘是他们厂副厂长的千斤。惠还绘声绘色地向小芳描述了新娘是如何追大张的。小芳听后,调侃道:“噢,原来是反弹琵琶呀,不错,时代不同了,谁追谁都一样!反弹琵琶伎乐天。”这是敦煌壁画上的一句话。
席间,新郎新娘敬酒时,小芳没有祝大张幸福美满,白头偕老,却祝大张鹏程万里,飞黄腾达。大张也没有“谢谢”小芳,却“嗨……”了一声。从那声“嗨……”里,小芳似乎也嗅到了一股怪味儿。
小芳结婚的时候,也请了大张、惠,还有别的几个同学。散席后,小芳和新郎送同学们离去,出了酒店,新郎止步了,示意小芳再送送。小芳一人又送出了一程。临别时,大张回过头来狠狠地冲小芳说道:“原来你喜欢小白脸!”边说边用力地眨了眨眼睛。小芳听了他这话,愣了一下。又见他那么用力地眨眼睛,想笑,却没有笑出声来,只咧了咧嘴。此时的大张听惠说已经快做爸爸了。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她和他再也不曾见过面。一晃,竟然快二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这些年来,小芳和惠一直保持着往来。虽然不甚密切,但一年里至少能通那么几次话。早些年,她从惠那里时不时能听到一些大张的消息。比如说大张的夫人给他生了个胖儿子;大张当主任了;大张当科长了;大张被破格聘高工了;大张出国了,去了德国;不知为啥两年多后又回来了;他们那个厂效益不好,大张回来不久就辞职下海去了广州等等。
起初,每次惠向小芳说起大张时,她还嗯、啊应承一下,后来随着大张的节节攀升,惠再向小芳描述大张时,小芳便不再做声,只是静静地听着。也许是惠从小芳的脸上读出了些什么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与惠交谈,开始绕开了大张,且形成一种默契,她俩说话时再也不去提及大张了。久而久之,大张从小芳的意识中淡出了。但小芳知道,惠肯定知道大张的动态。因为他们是姑舅。
星期六,小芳同往常一样,先是室内卫生,然后个人卫生,再洗衣服,再去超市采购、做饭等等。昏昏沉沉,忙忙碌碌一天。晚饭后,又到社区院子里跟着那些跳健身舞的阿姨大姐们扭着跳了一会儿,回到家后洗洗涮涮就过了十点。
一天来她竭力不让自己去想大张,可坐到床上后,由不得她又开始想了:张,除了大张不会有别人的。如果是大张,难道他也离婚了?他的儿子该上大学了吧?现在他在做什么?不过这些问题都好解决:明天给惠打个电话,不就可以问他个底儿掉了吗?
现在,现在做什么呢?对了,写条短信吧。她拿过手机,写道:
擦肩是十年的缘,
相识是百年的缘,
彼此交流是千年的缘,
成为朋友是万年的缘,
能携手共度,是永世的缘。
今日与君相遇,道是缘分几何?
昨夜无眠,我失眠了。今晚想做个好梦,也祝你好梦成真!晚安。
写好后发了出去。回信很快来了:
缘分永永世!希望你今夜不要再失眠了。早点休息,晚安!她拿着手机,犹豫了一下,又开始写短信:
如果说青年人的爱情,是季节催生的花蕾,那么中年人的爱情则是阅历精酿的美酒。成熟的中年人,不会像那些多情的少男少女,随意就扬起爱情的风波,也不会像某些深陷悲情而不能自拔的怨妇,让内心的爱情处于僵滞,进而将其打进自己精神的地牢……
她还想往下写,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座机的铃声。过去一看,是惠打来的。常听单位里有人这样说:这里的风很邪,说曹操曹操到。她几分钟前还想给惠打电话来着,惠却先打了过来。
“喂,现在不忙吧,打搅不?”惠说。
“不忙。这个点儿了,还有啥可忙的?今天想起打电话了?”
“不忙就好,跟你聊会儿。你可坐稳当了,你还记得大张吗,就我那姑舅?”
“记得。那能忘得了吗!他现在怎么样?好着吧?”小芳没有提及短信的事。
“还行吧。他现在跟你一样,很自由,一个人过着。”
“他离婚了?”
“早离了。小孩刚上初中他们就离了。开始时,他不是在广州吗,孩子跟妈妈一起过着。后来女方又找了一个,结婚了。男孩呗,死活不愿跟他妈找的那个一起过,又跟他过了。他也从广州回来了。孩子上高一他就回来了。我那侄儿挺争气的,去年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
“大张他现在干的啥营生?”
“他还行,自己当老板,开了一家电器商店,什么电话、DVD之类的,门面还不错。也算是小有成就吧。帮他打理店铺的是咱们一个同学的弟弟。小伙子挺精明的。
“他跟你联系过没有?今年清明节,我搭他的车去老家扫墓,我们来去一路上说的全是你。我看得出来,他对你满上心的,我就把你的手机号给了他。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忙?他说不用,他了解你,他自己跟你联系。
“上个星期天他又问我,我给他的你的手机号对不对?还问我你是不是换号了?我说没有啊。怎么?是不是打不通?还是打通没人接?他又吱唔了一下没说什么。他给你打没打过电话?”
小芳没有正面回答惠的提问,却说:“这么说他‘自由’也好几年了。这几年他没找吗?”
“临时的找没找,找了几个?我不知道。男人嘛!但正式的,绝对没找过。这一点儿我敢给你打包票。”惠说,“你想想,他回来这几年哪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事?先是买房子装房子,接着又找店面装店面,身边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他这几年确实也折腾得够呛。”
“应该说他这半辈子都折腾得够呛。”小芳打断惠的话说。
“就是就是,一点没错!现在总算稳定下来了。这不就想到你了吗?其实,这些年他一直惦着你。”
“你有他的电话吗?”小芳问。明知这是句废话。
“你拿纸笔记一下:他的手机号,一个是1385316****,另一个是1309215****;座机号。”“行了,有手机号就足够了。”小芳又一次打断了惠的话。接下去,惠又向她絮叨了许多许多,足足说了五十多分钟。等挂掉了惠的电话,小芳从手机上调出“Z”查看:“Z”正是1309215****。不错,是他,就是那个爱眨眼睛的大个子大张。她又是一阵心跳。以前小芳常说的一句话:逆境顺境,顺其自然;恶缘善缘,一切随缘。现在她却在想:这世上真有这样的缘分吗?(全文完) 写于2010.9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7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4 小路(三十 )
- 浏览:53 去红军苏区
- 浏览:53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48 樱花树下
- 浏览:48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2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329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90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5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9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6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5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58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6 换妻
- 浏览:16248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