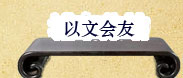无释无非(二八) 
第二天天不亮,荷花过来叫小兴。还有三个年轻女孩儿跟她一起,他从没见过,荷花说是她同学。五人步行走下四埠沟时有辆奔马三轮车过来,是个叫毋红举的十六七岁男孩儿租车接他们。到县城又换长途车到长垣火车站,下午上火车。沿路的票和午饭是荷花买的,小兴要拿钱她总是阻止,显得很热情。
坐了近十个小时的火车,凌晨三四点时在一个小县城下车。出站又坐辆破旧不堪的面包车,车身上几块比巴掌大的脱漆,副驾驶的车窗玻璃也揺不上。就在这么辆车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小兴在后座都晃睡着了。下车后天已经大亮,眼前是个比成家村破旧两倍的街道,不远处有段院墙是纯土砌的。车子冒着黑烟调头,他看到居然连车牌都没有。
荷花拍门的房子倒是挺整端,大门在蓝砖蓝瓦的十来间临街房中间。门开了,一个脸色黝黑的中年妇女笑着让他们进门厅,用近似河南话腔调喊了句什么。从七八米外另一排房里出来两男一女,笑着跑来跟他们打招呼。荷花两方面介绍,前面称作卢经理的四十多岁男人热情的跟小兴握手,跟后面的毋红举、董欣、董小洁、郭春燕握手,小兴也是第一次听他们学名。后面叫常总管的男人和没听清名字的女人也跟每人握手。
简单的介绍过后,三人连同荷花带小兴他们穿过中间的那排房,到后院角落的房子先洗漱,说马上就要吃饭了。看三人中两个男的出门往外走,荷花也要出去。小兴忍不住问:“荷花儿,你不说霞姐在这儿?人咧?”
荷花转身叫那女人巧枝姐,低头说了几句什么,他没听清楚。巧枝姐打量着小兴说:“小霞啊?出差了!得几天回来咧。”说的是纯正的豫北口音。荷花让他们洗过脸跟巧枝姐吃饭,她换衣服就过去。
小兴这才转身看房里,这是个两间半的拐弯房子。门口左边的窗子下有个水池,紧挨水池的台子上有十几个塑料杯子,里面是一样的彩色牙刷和两面针牙膏。三个女孩儿并排洗着脸。毋红举也在看,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惊讶。旁边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毛巾,每个毛巾上方都有个写着名字的标签,和杯子一样,看起来都像女人名字。门左边有个写字台,上面堆放着几本书和大小一样颜色类似的十几个硬皮本。后墙上没有窗子,墙皮有脱落的痕迹但一尘不染。靠墙是个整排的通铺在顶头拐弯呈L型,铺上是形色各异的床单,枕头放在靠墙叠放整齐的被子上。
吃饭的地方在后院另一边,门上用粉笔画着圈写了个“5”字。里面有二十多个男女围坐在铺满房子的草席上,除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其他都在二十五岁以内,看见他们纷纷过来握手。巧枝姐介绍他们:“这是咱新来的姊妹们,大兴,红举,春燕,小欣,小洁,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是小宋,这是二庆……”
究竟谁是谁小兴一个也没弄清,只是感受到这些人很热情。仍旧是围成圈坐下来,靠门那边巧枝姐旁边留了个空位。这里是个单间,房子里空荡荡没有任何摆设,靠门口窗边有个蜂窝煤炉子上放着冒白气的歪嘴铝壶。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副碗筷,正中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挨着小兴坐的董欣在他耳边问:“兴哥,这是弄啥咧?”他也纳闷扭头想问巧枝姐,因为她年长几岁也像这些人的头。这时,荷花出现在门口,已经换了一身红色棉裙,头发也盘起来明显描了眉涂过口红。其他人立刻鼓掌,像欢迎明星表演似的。
荷花进来先鞠个九十度深躬,满脸欣喜的感谢了七八个名字,喊两句类似口号的话,语速很快很兴奋,小兴能听清的只有“卢经理”“巧枝姐”。这时候,从外面进来三个人,把手里端的一个盆、一个托盘、一个竹筐放下转身就走。小兴仔细一看,这里的伙食可够赖的:菜就只有一盆白菜、粉条、豆腐、海带大烩菜和一盘炒芥咸菜,主食是馒头。小兴没食欲,就掰半个馒头夹了点咸菜。巧枝姐却盛大半碗烩菜笑着递给他,他不好意思就说声谢谢接过来。难吃,硬忍着才勉强吃完。吃过饭碗碟撤走,这些人又原样围坐在刚才的位置上。说是做什么游戏,小兴不想玩,想补个觉。
巧枝姐让个叫“老朱”的,看着比毋红举还小的男孩儿带他去寝室。所谓寝室门上仍然有粉笔写的“5”字,是一间十几平米旧屋,里面比之前去的更简陋,床都没有,就是一排草席上铺着褥子床单,被子和枕头还算整齐。唯一的摆设是门口小窗子跟前地上有个茶盘,里面摆着热水瓶和几个玻璃杯。老朱也很热情,让小兴在其中一个枕头躺下殷勤的盖上被子,还给他倒杯热水才关门出去。
小兴是真困,没几分钟就睡着了,被窝凉点也无所谓。直到老朱再次开门,叫他吃午饭,他才坐起来,穿上外套喝一口冰水跟出去。还是早上吃饭的那间房,还是那些人,荷花照样先发言,名字倒是听清几个全没听过。饭跟早上有点区别,两个大号钢种盆里分别装的土豆炖鸡块、白菜粉条豆腐,三个盘子是辣子炒豆酱、辣子炒芥咸菜、白米饭,竹筐里全是馒头。小兴心想:就这伙食,荷花儿还说赚钱咧,都不胜南海那破厂哩加班儿饭。想归想他没表示,毕竟他来是为了见丽霞,在不在这里干还是两可,等见面可以说服她一起去找大志。所以他没怎么吃主食,只是吃几口那些人客气时夹进他碗里的菜,米饭、馒头压根儿就没碰。
吃过饭碗碟撤走又玩游戏,小兴没兴趣,站起来还想睡觉去。巧枝姐旁边是个二十三四岁,身材消瘦留着剪发头的女孩儿。她问小兴平时玩什么游戏,他说不会,上学时玩过扑克也已经很久没玩了。巧枝姐说那就玩扑克,拉他坐下来打升级。接着有人拿出一副扑克牌,把大家分成四组,还真巧,正好二十八个人,认识的只有董欣跟他同组。四个人坐成十字,其他人都簇拥在各组玩的人后面。小兴这组自然他上场,本来他是不想玩,可巧枝姐和剪发头女孩儿的热情让他不好意思硬推。
几把牌过后,小兴明白他们不耍钱,得分少的整队做俯卧撑,心里稍微踏实点儿。一方面不想破坏那年答应大志不赌博的话,更重要的是担心这帮人合起来赢光他的钱,虽然只有两百多块,但输光肯定没法找大志也回不了家。又玩一会儿他觉得这帮人挺逗,最低和最高两个相差多少分,低的组就做多少俯卧撑,个个精神饱满不抵赖。他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跟他一起来的郭春燕和董小洁明显做不动,荷花和她们的组员却还在旁边齐声的打气,让她们坚持下去。其他三组人平静的跟没事儿人一样。还好他打牌向来手气好,这天下午硬是一把没输过,巧枝姐连连夸他聪明,组员也很亢奋。吃晚饭时,换成大半盆萝卜和一碗辣子酱,他还是少吃东西少说话。董欣坐在他身边时不时的飘过来一眼,眼神里隐隐是暧昧。
晚饭后换了个游戏。两两一组,其中一人闭上眼睛听同伴的指挥走过障碍,完了交换位置做,失败者要背成功者。人人参与他不好意思离开,尤其是巧枝姐一口一个“俺兄弟”,热乎的不忍拒绝。这次是剪发头女人跟他一组,他悄悄地问她为什么整天没见他们干活。她说她叫常小雨,他们的活就是在娱乐中进步,轻轻松松的赚钱。他不懂,她又说凡是来新姊妹都会先相处三五天,然后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他完全不明白,哪有不劳动就能赚钱的活?但他没空多想,因为这些人看哪组失败就齐声鼓励,有成功的就齐声欢呼。
到他俩的时候常小雨一不小心绊倒了,准确的说是他没把她带好,但她仍要背着他在刚失败的障碍圈里走三圈。看她单薄的身子背他都有点摇晃,显然很吃力,他怜悯之心来了,居然想跟她交换。但规矩就是规矩,她坚决不同意,艰难的走完三圈。董欣也够惨的,十六七岁的模样小巧玲珑的体型,好在她的伙伴也是女孩儿而且个头不大,但也够辛苦的。所以,临散场的时候她找荷花问,能不能下次把她和小兴分一组。荷花告诉她必须是一个师父带一个新姊妹,而且所有人都是姊妹不分亲疏远近,也就没得挑选。
一个地铺睡九个男人,包括毋红举都是白天在一起那些。身下有草席有褥子倒不很硬,就是冷,被子也薄的半天暖不热。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能倒头就睡,而且没过半小时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或许是他上午睡过的原因,又数羊又喝热水仍然睡不着。好容易迷迷糊糊的时候,好像听见窗外面有人悄声叫“兴哥”。他连忙穿上裤子披着皮衣到门外,一看很是吃惊,居然是董欣。她见了他竟小声抽噎,说冻得睡不着。这他能理解,因为他也一样,出门在外谁也不容易。可他又能怎样呢?安慰几句把皮衣给了她,她感动的用力搂他一下顺墙根跑回去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小兴感觉还没睡着多大会儿,听到外面闹哄哄的。睁开眼看铺上只有他一个人了,毋红举在旁边正穿衣服,看来也是刚醒。再仔细一听外面在唱歌:“……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处于好奇,他迅速穿好衣服。皮衣昨晚借给董欣了,上身就穿件毛衣来到门口看,真被吓一跳。毋红举在他旁边也一样满脸惊讶。因为院子里整齐排着至少两百个男男女女,把整个后院几乎站满了,正用洪亮的声音合唱着,而且都非常专注。因为他两个在门口站足有三分钟,硬是没人回头看一眼。离他们七八米远就是昨天那些人,郭春燕、董欣、董小洁也在荷花后面,声音太吵分不出哪是谁的声。
歌曲唱完是一阵激烈的掌声,这些人才分组有序的回房间。巧枝姐转身看到两人,小跑过来把身上的红羽绒服脱下来裹在小兴身上,很多人扭头看他们,把他弄得挺难为情的。洗漱的时候荷花领着董欣过来,把叠的整整齐齐的皮衣放在小兴提包上,然后替他把被子叠整齐摆好。荷花问他们睡的怎样习不习惯,小兴本来想发几句牢骚,毋红举抢着说“可好,可香了”,把他弄得不好意思说了,再说难听话显得小家子气。
早饭内容跟昨天没差别,只是荷花的话被巧枝姐代替了,内容几乎一样,感谢几个领导和在座的兄弟姐妹。饭后也是分组做类似的游戏,输的组不是做俯卧撑就是仰卧起坐,有的女孩累了可以用唱歌跳舞顶替俯卧撑。小兴也被罚做了三十个俯卧撑,累倒不累就是觉得无聊。午饭和晚饭也没区别,基本都是乏味的大烩菜和芥咸菜,晚上还有个清水似的面片汤。其实半下午时他已经感觉到饿,看到那些东西仍然没胃口。他悄声问常小雨,她说大部分时间是这样,有新姊妹加入时会加鸡或鱼。他彻底想放弃了,打算等丽霞回来无论跟不跟他走都要离开。晚上的游戏后半场也有点变化,让两两一组相互了解。跟他一起的还是常小雨,她说的详细程度把他给吓住了,什么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是男是女多大年龄,甚至连喜欢什么颜色的内衣,第一次亲嘴的对象是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动作都巨细无遗。这个他做不到,虽然他自负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却仍做不到,所以总是支支吾吾的。但她并不介意,反而笑着让他放松思想,放开怀抱。
类似的日子又过了四天,就在小兴到那里的第七天,他早起也开始跟大家一起唱歌。其实是从第五天起老朱天不亮就给他挤好牙膏、倒好洗脸水,晚上还有洗脚水。而毋红举已经跟老朱相互端洗脚水,他真不习惯被人照顾,只好主动起早自己做。对于那些乏味的饭菜和无聊的游戏更是无奈又不忍拒绝,每晚相互了解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真觉得没什么可讲,他就把发生在大志、国营、修建、杨文军、高玉林身上的事硬按到自己身上,每次掺插着说。
这天吃过早饭来到一间长筒房子里,一排排塑料凳子,顶头有台子有桌子还有黑板。在场应该有两百多人,他们同组的二十八人簇拥着坐了两排。巧枝姐给他们几个新来的发新本子和圆珠笔,告诉他们把认为重要的内容记下来,下午讨论。一阵很长很激烈的掌声后,有个穿蓝西装白衬衫打红领带的中年男人走到桌子后面,开始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在黑板上写数字。他也没听清说些什么,看不懂也懒得看,就是觉得整个过程很没劲。那人讲完又是激烈的掌声,接着又有人过去讲,都是些生面孔,介绍时不是某主任就是某经理。他压根儿听不进去,要不然在学校最后的日子也不用混着过了。好几次正打盹时就被掌声欢呼声震醒,懊恼之余再继续酝酿睡意,真有种跟一群疯子在一起的感觉。
讨厌的白菜豆腐汤喝完,没有专人收拾碗筷了,他们当中有人端两副有人端三副自己去水池子洗。老朱坐在那里没动还有意无意的扫视小兴和毋红举,两人对视一眼各自拿起眼前的自己洗去,因为他们看到郭春燕、董小洁、董欣拿起碗出去了。董欣跟小兴擦肩而过的时候小声说:“咋光顾自己哩?不说哩让相互友爱相互尊重咧?”
“中啊,那今个儿你先尊重我,改天我再尊重你。”小兴说着就把碗筷摞进董欣手里的碗上。
她赶忙扶住了碗,慌乱的扫视一眼别人,用更细小的声音说:“咦——不是说咱俩,是你哩那等。”说着还冲他身后刚刚起身的老朱瞥一眼。
他知道她暗示老朱,但觉得没必要跟一个小几岁的孩子讲相互尊重,只当没看见,而是开玩笑似的凑近她的脑袋说:“哎,你是不是也跟人家说第一回跟谁那啥啦?啊?”她幽幽地白了他一眼,说了句“我没”,端着碗快步走远了。也不知道是说没对别人说,还是到目前没发生过第一回。反正他是不在乎,只是随口扯开话题,悠然的站到门口点着一支烟。
毋红举反倒是注意到她回头动作,迅速回去接过老朱的碗筷,跟上郭春燕。
开始讨论上午听课的感想了,大家都很积极。除了小兴,他本子上的塑封还没拆开。巧枝姐第一个分享,把上台每个人的谈话重点都提到了,号召大家积极的学习。大家鼓掌后她点名让五个女孩儿三个男孩儿站起来分享,虽然没她生动也说的头头是道,赢来阵阵的掌声。她又让荷花与常小雨起来,分别点评那几个人分享的内容,随后分享她们的感受,她做全面的点评。
该新来几个人了,巧枝姐第一个点小兴的名字,并带头鼓掌欢迎。他本以为跟上午一样只需要混个过场,不自觉的犯困,听到点他名字立刻清醒了,却不知道怎么做从何做起,茫然地把目光投向荷花。荷花这次没帮他,而是笑呵呵地再次鼓掌说:“小兴哥啊,我看你上半晌就跃跃欲试了,给咱说几句儿呗。”他的脸腾就红了,心里不由得暗骂:哎呀,这半吊妞,你这是捧我还是踩我?荷花儿啊荷花儿,可真缺德啊你。心里不爽不能当众发牢骚,毕竟这帮称兄道弟的都大眼瞪小眼看着。无奈,他站起来挠挠头说:“我哩脑子不好使,嘴也不利索。不过我这人实诚,恁对我咋着我心里明白,就是不会表达。巧枝姐不也老说将心比心吗?我哩心拿出来是多大,放进去还多大。”说着把右手握成拳头在眼前晃了晃,“别哩不敢说,绝对是红溜儿哩!”这题都跑天上了,他却说的底气十足,而且还深深撇了荷花一眼,意思是:就你会耍心眼儿!
话音一落巧枝姐站起来,大声称赞:“俺兄弟说哩实在!中听!说哩好!”巴掌拍的山响。其他人自然也跟着站起来鼓掌,小兴的面子居然拾起来了,不管怎样算混过去,赶忙冲大家鞠个躬。
接下来郭春燕、董欣、董小洁、毋红举都说话了,也基本是说的上台某人的或几人的重要说辞。小兴这下全听清楚,什么“利用好身边的广阔资源”、“投入越多回报越大”“化人脉成金不是梦”都听得明白,但不知道这跟不干活赚钱有什么关系。至于后面老朱、荷花、巧枝姐对几人的点评,他全当成鼓励话一听了事。
这天晚上临睡觉前,董欣把他的本子拿去。连同她的本子抄两份巧枝姐的笔记,封面上“成大兴”的名字都是她代写的。
他们来的第十天傍晚,小霞回来了,一块儿回的还有她男朋友柳树林。荷花带小兴过去见她,就在他们来时卢经理出来那个房子隔壁。小兴一看有点似曾见过的感觉,但明显不是丽霞,所以想都没想就扭头瞪着荷花质问:“这就是你说哩霞姐?她是恁丁白庙哩霞姐?你当我傻啊?能就这诳人啊?”也莫怪小兴想发火,任谁跑那么远再成天吃那些没油水的饭菜都不爽,而且是拿他喜欢的人当幌子。
荷花也被吓一跳,反应过来为难地看看小霞又看看小兴,满脸不解的说:“她不是俺霞姐还是谁?小兴哥,咋啦?生啥气咧?有啥咱姊妹们还不能好好儿说?”
“你还敢说她是恁霞姐?你摸摸良心,敢说她就是丁丽霞?敢说她是小蛋儿婶她外甥女儿?”小兴听她咬准更生气,简直都想上手教训她。
“小兴哥啊,你弄岔劈了吧?她是俺霞姐没错,是我大大里外甥女儿也没错,可他不是丽霞姐,她是小霞姐,叫丁艳霞。”荷花刹那间弄明白了,可也傻了,她哪知道他想见的是大她八九岁的大姐?按他的年龄跟二姐熟识才合理。
那边的小霞丁艳霞也基本明白,但无论荷花怎么跟小兴说的现在已成事实,她只能尽量将他安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笑着转到他正面说:“我说老同学儿啊,你这是弄啥?见老同学儿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发怎大脾气弄啥?来来来,咱先坐下来再说话儿。”说着用手一拍小兴的肩膀,冲着荷花说,“荷花儿啊,去对面儿屋沏壶好茶。”
荷花转身刚要出去,小兴转身避开丁艳霞的手说:“那要是这,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我就不打扰了。”刹那间他也明白过来,想想确实他当时只顾高兴有丽霞的消息,压根儿没有进一步向荷花求证。既然弄清了也就没必要继续留下受罪,也不想再追究荷花诳他的事,他决定立刻去西安。说这话都没看丁艳霞,不管她是同学也好丽霞的妹妹也罢,终究不是丽霞。荷花走到门外停住了,听这意思小兴要走,哪有那么容易啊?刚刚稍微平静的脸上瞬间显露出担心的表情。
“呵呵,这是弄啥咧?”丁艳霞也显出几分不高兴,说到底她没把他怎么着,就算不是同学一见面就给她使脸色也不对。但她还是挺给荷花面子,毕竟他是荷花叫来的。再次笑着让座,“成大兴啊,不管咋说咱是同一届哩同学儿对吧?咱坐起来聊几句儿,叙叙旧,不多吧?”
“对不起,是我哩错我承认,我跟你真没啥聊哩。”小兴再次表明态度。
“你这意思是喜欢丽霞呗?她有啥好哩啊?成天光会做歌星梦。”丁艳霞不笑了,语气里还有几分不屑。的确,丁丽霞自从上大专走后,再没回去过,只是让同学给家里稍过一封信,气得父母哭闹好长时间,相互埋怨之后谁也不愿提她。从那以后父母对丁艳霞的态度大不如前,似乎料定女大不中留。遭的是她还没考上高中,父亲没征求意见就让她学缝纫,连成衣铺的后路都给她安排妥当。她对那安排极度不满,所以没上几天班就跟同学的姐姐找门路。后来跟同乡改枝姐到这里,接着结识了柳树林,目前在这里虽不敢说干的风生水起,但也是受很多人羡慕嫉妒恨的。
“对不起,喜欢谁是我哩事儿,跟旁人没关系。我走啊。”小兴说着转身往出走。听丁艳霞的语气明显是跟姐姐有分歧,但那是她自己的事情,不该在外人跟前数叨姐姐的不是。这也更让他坚定尽快离开的想法。
“你想咋就咋啊?当自己是老几咧?”有个响亮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正前面叫嚷,也是个接近河南话又不太像的。
小兴刚出门就被一个高个子堵住去路,没还看清模样先被溅到脸上几个唾沫星子,不由得退一步站到门旁边。看那人大概三十七八岁满脸的横丝肉,就知道不好惹,赶忙解释:“我也没招谁惹谁,就是不想干了,不中啊?”
“中不中不是你能说哩。”那人说着冲丁艳霞往里挥手,她转身进去把门关上了。那人又扭头喊:“继中,常继中,常总管。”
“咋不中?我吃恁几天饭给恁钱不中啊?”小兴有点害怕,就想尽快离开。
“哼,”那人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看着从后院匆匆走来的常总管,也就是小兴刚来那天进门见的三个人其中一个。那人不屑的说,“干活儿吧,让这货清亮清亮咱这儿谁说喽算。”说完径直到斜对面的房子,也关上门。
小兴还没来及弄明白怎么回事,从后面又来四五个人,二话不说和常总管一起摁倒他,扒掉皮衣往他身上头上拳打脚踢。事情发生的太快,他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只能连连求饶却不见他们停手。荷花也吓坏了,跑过来想劝,刚靠近就被常总管凶狠的目光瞪一眼,吓得的退到墙跟前蹲下,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不远处过道拐角还有几个脑袋探出来看,可没一个人敢劝,更别说出手阻止了。
作者简介:羽佳一鸣,原名翟自明,陕西籍自由撰稿人,作者,1978年生于河南新乡。著有长篇小说《爱的主题曲之阿莲》、《爱的主题曲之爱我你怕了吗》、《爱的主题曲之独家记忆》、《残梦惊情录》。诗歌有《虞美人·秋愁》、《虞美人·怀古忆佳人》、《玉兰愁》、《槐花赞》等数十篇,散文诗有《雨后》、《醒早了》、《晨雨浅殇》等数十篇,散文有《浅谈文字污染》、《小事更可为》、《秉烛夜读》等数十篇。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2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8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5 小路(三十 )
- 浏览:54 去红军苏区
- 浏览:54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48 樱花树下
- 浏览:48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5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2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343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91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7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9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8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6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60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6 换妻
- 浏览:16249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