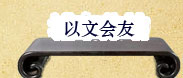内容
《浭水流》第一部第十章
《浭水流》第一部第十章 
达民跟着母亲到祖坟给爷爷烧完头七,回到家,见碾房来了好几个碾麦子的,才想起来今儿是小暑。浭阳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用当年的新麦子磨面,包饺子。愁云惨雾笼罩的张家也包了韭菜猪肉馅的饺子,如今老太太和张飞鹏那三个没娘的孩子都得王振芝一个人照顾了。淑英过来帮忙,达民也跟着凑热闹,仨人包了两盖帘。小达民手拙,包的饺子瘪了吧唧的,很难看。
“左撇子就是拙,看你包的啥?都得煮漏。”日子过得不如意,王振芝的脾气越来越坏,小儿子挨训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大娘,你说,老二这左撇子也没少打,咋就改不过来?”淑英问。
“还是打得轻。”说着,目光剑一般劈向达民。
王振芝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打,连写字都是用左手。但是如果他自己乐意干的事,不打也能改,例如使枪,左手不能用,很自然的就改成右手了。
到了傍晚,暑热也没散,吃完饺子的人们都摇着麦秸扇坐门外纳凉,王振芝去找王佬家,托她给淑英找婆家。张飞鹏被离婚官司弄得名声不佳,连累得闺女十七八了,都没人上门提亲。
像往常一样,达民跑到龙湾的白沙滩,跟小伙伴们玩打仗,一声高喊,“我是阎锡山,跟我一伙儿的站这边。”呼啦啦几个小伙伴站到他身后,他推了二印一把,“你是张作霖,谁跟他一伙儿站那边。”
两边排好阵型后,达民振臂一呼:“冲啊,打倒军阀。”身先士卒冲入敌阵,抓住二印扭成一团。
很晚,村庄才在蛙鸣中安静下来,人们或带着忧愁或带着希冀各自入梦,只有还乡河的流水还在奔淌。如果不是深夜的炮声,这个夜晚,跟千千万万个夜晚没有什么不同,张达民不会记得这天是公历的1937年7月7日。
就在人们熟睡时,卢沟桥的日军借夜色包围了宛平城,侵略者的炮声悍然响起,隆隆的闷响传到还乡河畔,惊醒宁静的村庄。酣梦中的小达民翻身坐起,跑出家门就见河堤上站满了惊慌的村民,人们凝神谛听,每一声轰鸣都像砸在头顶,身心随脚下的土地一起颤抖。这一刻起,即使是乡野村夫也意识到,中国已经没有退路,每个人都要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做出选择。
几天后,马贩子李希尧从北平逃回,在土地庙前被人群围住,“小鬼子太恶了,南苑那边遍地死尸,学生兵死了好几百,别提多惨了,被飞机炸得缺胳膊断腿。北平附近的村子都给烧了,连树都砍光,屋子里院子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
李希尧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有人不忍再听,转身走了,有的悄悄拭泪。
王佬家宝局,王子玉于令彻等人正在斗纸牌,王佬从土地庙回来,媳妇问他,“李希尧囫囵个儿地回来了?命挺大啊。”
王佬就把人们骂日寇的话重复了一遍。
“王佬,你别跟着起哄。”王子玉说,“李希尧就是反日分子,我要是把他说的,告诉周学礼,他肩膀上那小脑袋就得搬家。”
周学礼,南李庄人,丰润县日本宪兵特务队队长。王子玉在县城烟馆结识此人,臭味相投成了朋友,便在村里拉大旗作虎皮,到处炫耀。
“那你还客气啥?李希尧就是小人得志,赢了你的钱,还四处吹嘘,说你是他手下败将。”于令彻接口道,土地庙一向是他吹牛的地方,被李希尧抢了风头,让他很不受用,知道王子玉跟李希尧因赌博有过节,就煽风点火。
民族存亡的关头,有人奋起抗争,有人明哲保身,有人卖国求荣,国共两党都能捐弃前嫌共同抗日,却有睚眦必报的小人为泄私愤认贼作父。
一辈子舍身求义的张起鹏,从九一八事变,就一直在瞒着家人组织抗日。1938年6月,他辞了工作,前往丰润田家湾村参加秘密会议。会议上,李楚离传达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宣布八路军第四纵队在七月中旬挺进冀东,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冀东抗日联军。会议推举非中共人士高志远为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会议结束后,与会者分头回去组织暴动。
即将从城关高小毕业的张达民,准备报考滦县师范。就在他忙碌的迎接毕业大考时,父亲突然来到学校,“去找校长,马上退学回家。”扔下这句话就匆匆忙忙的走了。一头雾水的小达民只得去找校长:“我不参加考试了,退学回家。”校长惊讶地睁大双眼:“你疯了吧?还差几天就毕业,这时候退学?”达民言明这是父亲大人的命令,校长虽然不解,也只好同意。
拎着书包回到家,哥哥喜滋滋的迎出来,“我也退学了。”达民问母亲为啥让他们哥俩退学,“我哪儿知道,你父亲啥事跟我商量过?我连他去哪儿了都不知道。”王振芝气鼓鼓的回答。
几天后,张腾亚返家,还背回来一个大包袱,里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帜和红蓝两色旗及告示、袖标等。
“爸,这是什么旗?”小达民指着双色旗问。
“等会儿就知道了,你先去南院把你表哥李真叫来。”
张家房子是朝北开门,去南院要绕大半条街,达民习惯跳墙抄近路,墙根儿栽种了一垄窝瓜,瓜秧顺着墙攀援而上,金黄色的窝瓜花开了满墙。扒住墙头,一脚蹬住石头缝,另一条腿正要往上跨,身后就传来母亲的叫骂: “老二,你给我下来,谁让你跳墙的?把窝瓜都踩了。”
达民心里只有父亲交给的任务,对母亲的叫骂充耳不闻,翻墙跳进南院。李真是干妈的侄子,多年前就出外当兵,村里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他跟张家也算不上熟,跟长年在外教书的张腾亚更不熟,达民想不出父亲为啥找他。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在保守的村民眼里,当兵是不务正业,而且连年军阀混战,当兵基本上都是一去不返。李真是卢沟桥事变后,突然回村的,穿的便衣,还带回一台弹棉花的机器,回了家就每天闷头弹棉花,寡言少语、深居简出。
“嘣、嘣、嘣。”弹棉花机有节奏的响声和着棉絮从厢房飘出来,天气闷热,主人光着膀子,汗珠在肌肉发达的胸脯上滚动,听到有人进来也不抬头。达民提高嗓门压过棉花机的声音,先叫了声表哥然后说:“我父亲回来了,叫你过去一趟。”李真这才抬起头,面露喜色:“回来了?回来好,我马上过去。”
达民又翻墙回家,见父亲还在整理满炕的标语袖标,两个堂兄和哥哥也被派去找人。过了一会儿,院子里进来一个英武的军人,穿一身洗得发白却熨得平平整整的国军军服,腰系武装带,身背盒子枪,腰板笔直,精神抖擞。进了屋,一个立正,“报告,李真到。”
“李真?”达民定睛一看,可不咋的,真是李真,这才是真实的李真,跟刚才弹棉花那个判若两人。
又过了一会儿,李贺也扛着他家的步枪来了,陆陆续续又有七八个人到来,有本村的,有外村的,都带着武器。孩子们帮着分发袖标,将旗帜插上旗杆,一切准备妥当,张腾亚示意众人站成一排,他自己站到屋子中央,举起右拳庄严宣布:“罗文口抗日联军成立。”李真带头,大家鼓起掌来,达民他们哥几个虽然不明就里,被气氛渲染,也跟着使劲拍巴掌。
张腾亚领导的罗文口抗日联军高举抗联两色旗,从张家大院出发,掀开罗文口抗日暴动的序幕,暴动的第一场战斗是夺取本村政权。
村公所在南庙前殿的厢房,房顶上插着冀东自治政府的旗帜,由村里的保安队守卫。张腾亚一行人斗志昂扬的闯进去,保安队毫无防备。
“中国人不能给日本人卖命,不能当亡国奴。你们要么投降,要么以汉奸论处。”张腾亚义正词严的宣布。
“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也想抗日,能加入你们不?”一个保安队员询问。
“抗日统一战线欢迎任何人加入,你们悔过自新,参加抗日,我们当然接纳。”
保安队员们一听,立刻欢呼,爬上屋顶拔掉冀东自治政府的旗帜,插上抗联的红蓝两色旗。
罗文口易帜!一阵劲风吹来,抗联的旗帜猎猎飞舞,张腾亚一声招呼,全体登上大殿屋顶,站到旗帜下,高唱《卢沟桥歌》:
“卢沟桥!卢沟桥!
男儿坟墓在此桥!
最后关头已临到,
牺牲到底不屈挠;
飞机坦克来勿怕,
大刀挥起敌人跑!
卢沟桥!卢沟桥!
国家存亡在此桥!”
天空澄澈碧透,一轮烈阳凌空高照,赤焰迸射、还乡河浮光烁金,飒飒风中,雄壮的歌声久久回荡,听到歌声,村民从四面八方涌来,集合到旗帜下。
“我们参加抗日联军。”张国权带着王振川等几个好友前来报名,并从这天起更名为张一民。
初战告捷,队伍扩大,罗文口抗日联军意气风发的又去附近村庄招人收枪、解散保安队。仅用几天的时间,就集合起三百多人的队伍。
又过了两天,还乡河上游的抗联队伍乘船到来,接张腾亚等骨干去南边跟洪麟阁汇合。据张达民记忆,冀东抗联的番号是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总司令高志远。副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三人各率一路军。张腾亚任洪麟阁部一总队参谋长,队长是裴善之。洪麟阁部还设了八大处,张飞鹏化名罗春一担任军法处长,医务处长是杨效昭,政治部主任杨十三的女儿,后与李楚离结为夫妻。张一民和王振川被编入卫队,负责保卫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谷云亭。十六岁的张伯民加入邓宋支队即八路军四纵队,被编入宣传队。李贺是洪司令的卫兵,他堂兄李真是卫队长。
抗日暴动一呼百应,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连土匪绺子都纷纷加入抗联,其中就有光棍于邦。于邦当年因张贴讽刺显大人的打油诗造其陷害,被捕入狱,差点被判死刑。幸运的是,得到侠义的周逵帮助,替他找了个律师,律师发现验尸报告上写女尸脖颈有两道勒痕,很明显于邦门前的老榆树不是第一现场,分明是移尸陷害。所以,于邦蹲了几个月牢后就被释放,出狱后的他就投奔了狱友,落草为寇。如今,国难当头,绿林好汉们也金盆洗手,下山参加抗日。
看着亲朋好友都参加了抗联,老张干也不肯落后,他来找小达民。
“老二,你教教我咋使枪,我也打鬼子去。”
达民听了哑然失笑,看林子的老张干不会使枪,因为,他那双牛眼睛总是同时开闭,永远做不到一睁一闭,没法瞄准,达民咋教都是白费功夫。
“这样吧,你用膏药粘上一只眼。”达民戏谑道。
“妈拉巴子的,臭小子耍我。”老张干最终放弃了成为抗联战士的梦想。
抗联队伍对所有参加者敞开大门,因此成分复杂,纪律涣散,个别人以抗日为名抢夺百姓财物的事也时有发生,被群众称为“横眼翻”,意思是横眉竖眼的进屋就翻东西。没有军装,武器装备也都是自带,是名符其实的“便衣队”。虽然人数多达几十万,战斗力却十分有限,每场战斗都是伤敌八百自损三千,牺牲者的鲜血染红义旗、染红浭水。
几十年后,笔者听祖母和几个老太太闲聊,她们说,“起便衣队那年,一打仗,河上面飘的都是死尸。”听到这话,笔者幼小的心忍不住悸动。如今的我,时常会想,那些死去的便衣队员,他们的遗体有人打捞吗?有人安葬吗?他们在战后获得烈士称号了吗?他们的坟墓有人祭扫吗?如果没有家人,会不会没有坟墓?会不会早就被遗忘?会不会有抗联战士的白骨跟鹅卵石一起沉睡在深深的河底,直到今天,直到永远?
作者简介:业余写手。冀东人。
上一篇:特高课在仓阳七十四光临指导
下一篇:特高课在仓阳七十三能发现这个内奸吗
发表评论


分享本站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2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8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5 小路(三十 )
- 浏览:54 去红军苏区
- 浏览:54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48 樱花树下
- 浏览:48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5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5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2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351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94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7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9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701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7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63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6 换妻
- 浏览:16249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