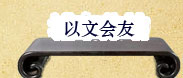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浭水流》第一部第十六章 
纪实体家史小说《浭水流》第一部抗战篇 血洒冀东
第十六章 血染冰河
“不就是觉得你父亲没了、张家落魄了吗?我要让他们看看啥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王振芝拽着伯民去了陈家,一进门,就把一袋子银大洋拍到炕上,“亲家,把这笔款存你们药铺,留着办婚礼。”说完,扬起左手正了正头上的绒帽,手腕上闪烁的金光,晃得玉玲娘眼花缭乱。
“玉玲,妈早就跟你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伯民他妈手腕上那个金镯子,少说也有二两重,城北寨杨家的外孙女,拔根汗毛都比咱腰粗。”张家母子走后,娘给闺女吃定心丸。
其实王振芝陪嫁的首饰早都卖光,那镯子是铜的,用酒精灯烤出亮光很像金的。几百大洋和一个铜镯子就唬得陈家同意嫁女,但提出要把婚礼办得风光体面,不光是酒席要摆在宝星饭店,还要用最时髦的形式接新亲——坐汽车、穿婚纱,王振芝一一应允。这场豪华婚礼办完,卖房子卖地的钱花光,寄居的旅店催房钱,伯民问咋办,王振芝一磕烟袋:“给你表姑父写信。
表姑父就是周逵,接到信立马给寄了四百块。有了这笔巨款,伯民真把自己当阔少,辞去照相馆的工作,穿着锃亮的大皮鞋,坐旅店拉二胡,小两口尽情享受蜜月。
母亲和哥嫂在秦皇岛摆阔装富时,达民负了伤。
1940年12月26日,达民带警卫班护送谷部长和几个出纳去丰润小营村收款。前几天降了雪,坑穴溜洼一片莹白,谷部长穿着张家送的狐狸皮大氅走在前面,达民缩着肩膀紧紧跟随,凛冽的北风中单薄的军服就像穿了层纸。 返回时行至亢各庄,天色已晚,部长决定住宿。冻了一整天,能躺在热炕上,舒展四肢,安然入睡,是打游击的八路军难觅的幸福。可这幸福对达民来说实在太短,一大早,村干部就来报信,说县城的敌人要出来扫荡,具体都到哪个村庄不清楚。于是谷部长就决定分散隐蔽:“我们几个就留在这儿,小张你带三个人去罗文口。”
罗文口抗日政府的村长国泰(本名于志波),是达民的好友,“王云照家最近挖了个很大的地洞,他家又有人在伪治安军里当官,比较安全,就住他家吧。”
“他家有伪军,不会出卖咱们吗?”达民有点不放心。
“他不敢。”国泰很有把握,“锄奸队这一年没少埋,即使他有那心也没那胆。”
王云照的祖上是武举,武举的大刀如今作顶门杠。尚武的达民对那把刀很好奇,今日能迈过王家的高门槛,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进门就看刀。此刀就是评书里说的那种“青龙偃月刀”,长杆、刀头为半月形。达民试了一下,单手举不动。正在诧异古人的臂力,王云照解释说,这刀有八十多斤,是武举练臂力用,太沉,不能用于实战。说完催促他们赶紧下地洞,地洞很大,用于围庄时藏财物,他家虽然有人当伪军,也护不住,鬼子想抢东西才不管你是谁家。
达民让另外三个人先下去。
“一起进来吧,让王家封洞口。”地洞宽敞,藏三四个人绰绰有余。
“不行,我还得去亢各庄,看看部长他们咋样。”达民坚持亲自封洞口,感觉万无一失,才从北面出村,然后向东走。他认为县城在南面,敌人肯定从南面过来,所以,从东绕到敌人后面,再去亢各庄。却不知这次敌人提前下了公路,先去的亢各庄,他这么走等于自投罗网。
两村相距二里路,走到一半,对面过来一辆拉粪的车,车上坐着于邦。
“老二,你咋还不快跑,敌人来了。”于邦看见达民就喊。
随着话音一排自行车从亢各庄飞驰而来,达民转身就跑,敌人在后面喊了声“站住”,紧接着就开枪。
一声声枪响,一颗颗子弹掠过,达民感觉左腿一热,有个东西“嗖”一下穿了过去,“负伤了”,脑子里念头一闪,马上感觉左腿发沉,不敢停,拼命朝河跑,边跑边还击,很快就打光了枪里顶上堂的七发子弹。他一还击,特务们就减慢了车速,使得他能跑到河边。数九天的还乡河冒着寒气,浮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把枪掖进怀里,毫不迟疑地扎进河中,水面立刻泛起起一片殷红。冰冷的河水很快浸透棉衣,像针扎一样刺痛,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此时的张达民只有一个念头:游,游。河面也就二十多米,对岸却遥不可及。一下,再一下,不能停。四肢越来越僵、越来越沉,心里喊着,“近了,近了,坚持住”。
特务们追到河边,下了车,你瞅我我瞅你,谁也不肯下水,虚张声势的朝河里打了几枪,转身走了。冰河里的张达民咬紧牙关,终于凫到对岸。爬上河堤,被冰水浸透的棉衣塌到身上,冷风一吹,迅即结冰,像厚厚的铠甲。怕敌人绕到桥上过河,他朝最近的宋各庄跑去。冻住的衣服箍在身上,随着跑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疾跑凫水再加上失血,他的体力消耗殆尽, 心脏狂跳,胸腔痛得似要炸裂,受伤的左腿已经麻木,仿佛跟身体脱节。眼前一阵阵发黑,头脑发困,只剩一个念头:跑、跑、跑……。村子的轮廓渐渐清晰,太渴了,嗓子冒烟,水,水,一口就行,只要一口。到村头了,老天啊,终于到了。第一家,闯进去,灶膛里一个妇女正在低头洗地瓜。
“大姐,给口水。”吃力地用嘶哑的声音勉强吐出这几个字。
农妇抬头,“妈呀!”一声惊叫跑进屋。不是农妇胆小,是张达民的样子实在吓人。伤腿流出的血把鞋灌满,又从鞋里溅到脸上,再从脸上淌到胸前,整个人鲜血淋漓,蓦然冒出个血葫芦,谁都会失魂落魄。妇人的尖叫让张达民昏沉的大脑清醒,顺手抓一个地瓜转身就跑,边跑边咬了一口,“我的妈呀,咋这么苦?”,一口吐出。其实不是地瓜苦,是他失血太多,血容量不足造成的干渴导致味觉异常,这种症状的出现是休克先兆。那时的他并不懂这些,把苦地瓜扔掉,还想再跑,但是已经彻底没了力气,头晕眼花,困倦得想躺地上睡过去。“不能躺,绝对不能,躺下就完了。”残存的理智提醒他。
再也跑不动了,就拖着伤腿尽力的快走,好在村边不远就是山坡,山坡上有一片坟地,似乎有人站在高处,他想呼救,可嗓子发不出声音。
站高处瞭望的是看坟老人,他听见枪响,就出来察看,看见八路跳河,他就到高处瞭望,见达民从村里朝坟地急忙跑,老人迎过来:“八路,我背你。”
“得救了。”精神一松,整个人就瘫倒老人背上。老人把张达民背到看坟的小房子里,帮他脱下湿透的衣服,躺到热炕上。真暖和,裹在被子里,更困了,无数的金色的小星星在眼前闪烁。
“敌人也许会追来。”一个激灵,使劲睁开眼,对老人说:“我身上还有几发子弹,实在是走不动了,特务要是追来,我就只能在这里打了。”
“孩子,你放心,这儿是坟地,没别人。我先给你把伤口扎上。”
贫穷的看坟老人从被子上撕下一条破布,子弹是从膝关节上方穿过,经冰冷的河水浸泡,血已经止住。
“不出血了。”老人欣慰地舒了口气,听他说口渴,老人就烧了点开水,给他冲了碗淀粉。
见八路喝完淀粉,惨白的脸色稍微好转,老人就去报告村干部。第二天,敌人撤走,亢各庄的村干部赶着一头小毛驴来接伤员。
谷部长见了达民,劈头盖脸一顿批评:“你这不是惹祸吗?你和别人一起下到地洞不就啥事都没有?没把命丢了就算幸运。可真是个捅毛蛋的,到哪儿都惹麻烦。当初就不该要你。”
达民强忍着伤腿的剧痛,一声不吭。这次,他没反驳,没辩解,在十二团的经历让他终于懂得了上级是不能顶撞的!
“这样吧,你回家养伤。”沉吟片刻,谷部长做出决定。
回家?达民不禁心中一凛。“部长,我妈去秦皇岛了,把房子和地都卖了。”
“是啊,部长,这孩子回家就没饭吃,给他带点钱吧,还得治伤。”旁边的人也帮着求情。
谷部长就从收的款里拿出三百块,给了达民。亢各庄的村干部用小毛驴把半死不活的张达民送回罗文口。
张达民此次负伤是不幸,却因祸得福,避免了被谷立之牵连。在他回家疗伤后不久,他负责保卫的部长突然潜逃。谷立之贪杯,即使在艰苦的抗战中也要天天喝啤酒,为饱口头福挥霍很多公款,眼看窟窿越来越大,他就跟老婆商量咋办,老婆说卖房子卖地也要把钱赔上。他却担心被组织知道后受处分脸面不好看,竟然夹带一部分钱逃到北平,买了几辆洋车开车行。丈夫逃走,老婆在家陷于两面夹击,在日伪看来她是八路大干部的家属,在抗日政府眼里她是逃犯之妻,女人走投无路只好上吊自杀。谷立之既是冀东抗日大暴动领导人谷云亭的亲戚,也是很早就叛变的谷兰亭的亲戚。谷兰亭想争取谷立之,估计他过段时间肯定回家,就派人在火车站蹲守。不出所料,谷立之果然返家,一出站台就被捕,在谷兰亭劝说下投敌,后被锄奸队处决。如果达民不是负伤离队,作为警卫班长,他肯定要为谷立之的叛逃担责。
“你不能回家,最近,鬼子天天来围庄,你家目标大,还是藏王家地洞吧。”国泰说。达民点头同意村长的安排。
“你伤成这样,得有人照顾。王家能让你住地洞,可人家不能照顾你的吃喝拉撒啊,这可咋办。”国泰皱眉蹙额。
“找我姐吧。”达民无奈地说。
淑敏接到国泰送来的口信,马上赶回娘家。在王云照的地洞里藏到第二天,张达民开始发烧,破布条裹着的伤口渗出脓水,腥臭的气味在地洞里弥漫。
姐姐找国泰商量,“得赶紧找大夫,要不然,我弟这条腿保不住。”
“大姐,我也着急啊,我看这情况,不光是腿保不住,再找不到大夫,连命都保不住。”
不是没有大夫,而是没有敢给八路治伤的大夫。国泰四处打听,终于探听到泉河头有个叫韩伟的西医,暗中医治八路伤病员。第三天夜里,韩伟来到,检查了伤口后,连连叹气。
“大夫,还有救吗?”张淑敏急切地问。
“有,但是,小伙子,你得咬牙挺住,我可没有麻药。”
“不就是疼吗?关公能刮骨疗毒,我这点疼算啥!”张达民豪气冲天的说,“来吧!”
没有外科手术工具,韩伟用纱布条穿过伤口来回的扯,将腐烂组织磨掉。关公刮骨疗毒时,华佗发明了浓酒配制的麻沸散,虽然其效力不如现代的麻醉剂,但肯定也是有一定作用的。而张达民连酒都没喝一口,就这么硬挺,没几下,就痛得昏了过去。
淑敏大叫:“大夫,不行了,人不行了。”
“别慌,是疼晕了。”
用银针刺人中后,张达民醒了过来,揩了把额头冷汗,嗫嚅着问:“好了吗?”
“好了,马上就好。”韩伟也松了口气。去除腐烂肌肉之后,用雷夫奴尔纱条把伤口填塞,让肉芽一点点长出将窟窿填满。仗着年轻体质好,没用任何消炎药,命硬的张达民当天体温就降了下来。
看着弟弟一天天好转,淑敏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她托人写了封信给秦皇岛,希望母亲能回来。达民也盼着伤腿快点好,他不愿拖累姐姐,也感觉该换隐藏地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达民负伤的消息已经在村子里传遍,随时可能被泄露给敌人。
作者简介:业余写手。冀东人。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4 小路(三十 )
- 浏览:53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2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7 樱花树下
- 浏览:47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0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297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9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1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8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0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4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50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5 换妻
- 浏览:16248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