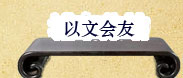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浭水流》第一部第二十二章 
纪实体家史小说《浭水流》第一部抗战篇 血洒冀东
第二十二章 走投无路
达民接过枪,转身就走,一秒都不敢滞延、唯恐生变。出村前不敢走太快,做出病痛的样子,出了村口,立即隐入山中小路,两腿生风的疾走,恨不得生出双翅
张家门口,停着一辆马车,韵秋正带着几个妇女在车上做军衣,季荣也在其中。
“你们看,那不是二哥吗?”眼尖的丽珍指着街口走过来的人叫道。
季荣见了,又惊又喜,刚想说话,又羞红了脸,埋头做针线。
“这么大的风,你们为啥在车上做衣服?”达民问。
“鬼子要扫荡了,不定啥时候就围庄,我们在车上方便撤退。”韵秋抢着回答,一指披霞山,“你看见没?山顶那棵树,那是信号树,老张干在山顶,看见鬼子出城,就把树放倒,看见树倒,我们就赶着车往山里跑,一分钟都不耽误。”
“嫂子,快回去给二哥做点好吃的,看他都瘦成啥样了。”丽珍把季荣手里的军服拿过来,催促她回家。
季荣看着形容枯槁的丈夫,眼泪差点掉下来。可此时的张家,已衰败凋零到三餐不继,靠着伯民微薄的薪水,别说给达民加营养,连填饱肚子都难。玉玲受不了日子的清苦和鬼子抄家的惊吓,带着孩子回了港城娘家。听到张飞鹏父子的死讯,淑英和小花旦抱在一起恸哭,胖胖的婶子面无表情,夜里却发出压抑的哭泣声。
“你婶子也够可怜的,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你父亲劝他们和好了,好心做了坏事。”王振芝一声长叹。张飞鹏本来就对包办的婚姻不满,工作中又跟某村一个风流的妇女主任相好,铁了心要离婚,是张腾亚在郭庄子隐蔽时,见弟媳在娘家处境尴尬,动了恻隐之心,苦口婆心的劝解弟弟,逼着他把媳妇接回来。勉强和好后,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王振芝总宽慰妯娌,说男人到了一定岁数就能收心。小花旦嫁过来后,胖婶的心落稳了些,儿子都娶妻了,当父亲的还好意思离婚?然而希望的曙光比闪电消失得还快,张化鲲的横死掐灭了她最后一星希望。心如死灰的胖嫂,寿命挺长,孤独中过了几十年食不果腹的日子,没儿没女,也没了那身胖肉,松弛的皮肤耷拉着,到了步履蹒跚的晚年,为了能从生产队分到口粮还得去挣工分,发霉的地瓜干都长了半寸长的绿毛,也舍不得扔,那是青黄不接时的救命粮。连个灯泡都买不起,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在用煤油灯,为了省油,灯芯捻得极细,黄豆粒那么大的一点亮光,照着一张没有悲喜的脸,见了人也不说话,木僵僵的。土改时分了间偏厦子小草房,阴暗潮湿,终日不见太阳,到了连阴雨的季节,房顶都长出蘑菇。冬天四面透风,下雨到处漏水,摇摇欲坠
地挺到1976年,地震中轰然倒塌,成了她的坟冢。
为撰写家史,笔者向亲友询问她的姓名,竟然无人知道,甚至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张飞鹏这个续弦的命运,实在悲哀。而张一民的小花旦,命运更加不堪,甚至可以说比黄连还苦。
“妈,趁他父亲还没来接,你赶紧给小花旦再找个婆家吧。”韵秋跟娘说,“我担心舅舅再把她卖了。”
“不容易找啊,这几年,鬼子杀了那么多男人,黄花闺女都难嫁,别提寡妇了。”
韵秋娘说的没错,战乱中的女人想找个好婆家,属实不易。成了孤女的淑英,很有主见,也很有胆量,自己找了个泉河头的郎中,虽然贫穷,也算是个归宿。小花旦想跟婆婆一起在张家守寡,可狠心的父亲岂能放弃拿闺女换钱?很快就把她卖给小陈庄一个做豆腐的当小老婆。大老婆凶悍,刚进门就给她个下马威,劈头盖脸一顿大,“知道我为啥打你吗?是给你规矩。你在亢各庄的丑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如今你那当八路的野男人做了鬼,可再没人给你撑腰,不守规矩,就是死路一条。”
在大老婆的淫威下苟且偷生的小花旦,整日以泪洗面,一双杏眼哭成烂桃,而且肚子不争气,到了冬天也没怀上孩子,男人感觉钱白花了,成天不给她好脸色,大老婆更是非打即骂。到了冬天,连双棉鞋都没有,三寸金莲生了冻疮,战战兢兢地乞求大老婆给买点药。
“真是千金贵体,生个冻疮也要上药。”
“肿得跟紫萝卜似的,一沾地就疼。”小花旦说着,眼角溢出泪水。
“还哭上了?谁虐待你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娇贵”
大老婆说着,狠劲地猛踩小花旦的冻脚,疼得她直冒冷汗,大张了嘴却喊不出声。肿胀的双脚被踩破后,溃烂感染,不停地流脓淌水,一沾地就像钢针扎心,她只好跪在地上爬着做饭洗衣喂猪。曾经的花容月貌,荡然无存,憔悴不堪模样,男人也看她不顺眼,在无端又挨了一顿打后,万念俱灰,用点豆腐的卤水结束了飞蓬断梗的一生。
笔者常想,如果张一民不死,论资历,建国后也能混个县团级干部,小花旦若是跟着他参加工作,凭美貌和文艺底子,说不定能进文工团,他们俩青梅竹马的爱情比《父母爱情》里的那对,差不到哪里去。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生逢乱世,又摊上吸食鸦片的狠心父亲,弱女子如浪涛里的一茎细草,掌控不了命运,只能盼早死早托生。
敌人已经从南向北开始扫荡,“汪派国民党”事件却并未结束,打击面之大,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因是罗春一的侄子,张达民虽被释放,区里却不敢给他安排工作。没工作,没收入,达民不得不为一日三餐发愁。
大扫荡中,日寇丧心病狂,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村民无论是不是八路亲属都弃家而逃,当时叫“跑敌情”。成百上千的难民逃到罗文口,各家各院都住满,连牲口棚柴草垛甚至牛车上都满满是人。除了住还得吃,村里很多人家都开始卖饭。
“王佬家发财了,他家的油条豆浆一会儿就抢光。咱们要是会炸油条肯定也能赚钱。”王家哲对达民说。
“张志发的弟弟张云亭会炸油条。”达民突然想起,“我去找他,咱仨搭伙卖油条。”
三个好友的油条铺很快开张,生意红火,可就是不赚钱。达民打游击时认识的外区外村的抗日群众,或者穷或者逃的急身上没带钱,只能赊账,达民不好意思像王佬家那样心狠脸冷的不赊,所以,油条虽然不愁卖,却收不回钱,很快就入不敷出。不只是生活难以维持,还有更坏的消息传来——爱写匿名信的雨风当了副区长。
黑白颠倒正义蒙尘之时,奸佞小人如鱼得水飞黄腾达。雨风上任,抓“内奸”之积极到了疯狂的程度,连普通抗日群众都成了“汪派国民党”,每天要抓捕的人数之多,忙得交通员马不停蹄地传送名单。
罗文口的交通员是老张干,每天早晨都要在披霞山路口一块巨石上等候区交通员,把纸条送到村里交给国泰和马百春。这天,他照常把名单送到土地庙的村委会,马百春接过一看,不禁哑然失笑,“不识字的睁眼瞎,把自己的逮捕令送来了。”
刚走到门口的老张干被几个民兵扑上去,绑住双手拴在香炉腿上。
“操你祖宗。绑我干啥?抱你儿子跳井了?”老张干破口大骂。
“还敢骂人!”马百春上去扇了老张干一个耳光。
“别打人啊,他这么大岁数了。”国泰劝阻。
让老张干坦白交待同党,他听不懂啥叫“同党”,问他都发展谁了,他也不明白啥叫“发展”。
“就是问谁领导你,你领导谁。”马百春解释,见他还是一脸懵,就说,“就是你听谁的,谁听你的。”
“我听区长的啊,谁听我的?我他妈大字不识一个,谁能听我的?”老张干喘着粗气说,“我黑介白介,就是看信号树,送信。从来没耽误过。别的事,不懂,也不干。啥也别问我,问也知不道,要打你就打,要杀你就杀。”
碰上这么个榆木疙瘩花岗岩脑袋,国泰又拦着不让打,马百春只好派两个民兵看押,等雨风区长的指示。到了晚上,两个民兵扔下老张干跑到对面的王佬家打牌喝酒,后半夜回来倒头便睡,到早晨还酣睡不醒。天光放亮,到了接信的时辰,老张干心急火燎,挣扎了几下,手臂的绳索竟然松开,不由大喜。
吃过早饭,马百春就来土地庙,见大门洞开,香炉腿上只剩绳子,两个看守鼾声如雷,气得他大骂,急忙召集民兵准备搜捕。
“搜啥?压根也没跑。”国泰拿着信,身后跟着老张干。
“信接到了,没耽误事。”履行完交通员职责的老张干伸出双臂,“给爷爷再绑上吧。”
“这样的人能投敌当汉奸吗?”国泰向区长雏燕汇报。
“放了吧。”雏燕大胆做主,老张干恢复自由,还当交通员,继续负责看信号树和接送信件。几天后又有抓捕名单送达,这次竟然是马百春。
村干部被检举,由区里审问。审别人很刚的马百春,轮到自己却软得像面条,没挨几下,就疯狗似的乱咬一通,把罗文口参加过抗日活动的村民都给说成内奸,一口气供出好几十个。
雨风如获至宝,吩咐罗文口的村干部国泰和李云列出详细名单。
“你再说一遍,同党都有谁。”国泰不会写字,负责询问,李云记录。
“第一个,张达民。”马百春说。
国泰一听,使劲打了他一耳光,提高嗓门问,“小张真是吗?”
“不是,不是,我刚才糊涂了,是瞎说。”马百春立即改口。
“还有谁?”
“王家哲。”马百春又乱咬。
雨风带着武装大队,按名单抓人,到罗文口先奔王家,刚好王家哲上山干农活没在家。
“丽珍,快去告诉你哥赶紧跑,越远越好。“家哲娘一看来头不对,一边吩咐闺女送信,一边迎上去在大门口拦住雨风,“哎呀,这不是雨风区长嘛,今儿咋这闲在来我们家?也没啥好吃喝招待,就尝尝自家做的麻糖吧。”
机灵的丽珍假装进屋取麻糖,迅疾跑向后门。雨风推开家哲娘带着人往里走,家哲媳妇端着麻糖迎上来,婆媳俩热情地扯住雨风非要他吃。
“王家哲呢?”雨风捏了块麻糖。
“拉肚子,蹲茅房呢。”家哲娘说,又吩咐儿媳烧水沏茶。
丽珍到了西山坡老远就喊:“哥,雨风来抓你,快跑。”
“往哪儿跑?”王家哲犹豫不决。
“妈说越远越好,就去北平吧,投奔二姨。”
“身上一个钱都没有。”王家哲犯难。
“你咋这笨啊?到县城,找三叔,先借着,过几天,我和妈去还,别啰嗦了,快溜地。”
王家哲扔下锄头,穿小路直奔丰润县城。
国泰偷偷来找达民,“今儿是雨风不在场,我能救你,下次就不一定了。”
怎么办?坐以待毙还是避走他乡?留下是引颈待戮,逃,又无处可去,张达民一筹莫展。更奇怪的是,张云亭也连日未见踪影,三个人的油条铺不得不关门。
疑窦丛生的达民,正想去南关张志发家里问个究竟,韵秋风风火火地跑来,“二哥,出事了。”
“出啥事了?快说。”被她的情绪感染,达民也紧张起来。
“张云亭投敌了。”
“什么?”简直是晴空霹雳,抗日英雄张志发一奶同胞的亲弟弟,竟然投敌,这怎么可能?达民难以置信。
“是区里公布的,张云亭听说他哥被活埋就投敌当了伪军。”
“你刚才说啥?张志发被活埋?”又是一个霹雳,震得达民脑袋嗡嗡作响。
达民被县委带走后,泉河头区又有很多干部相继被逮捕被活埋。更令张志发不满地是盟兄杨某的遭遇,他们同为节振国的结拜兄弟,一起参加抗日。杨某受伤后被敌人抓到,充劳工押送东北,途中逃脱,历尽艰险回到家乡,却被诬为投敌,给活埋了。情绪低落的张志发,不再组织突击队打击鬼子,而是经常到东马庄跟那个相好的寡妇厮混。寡妇婆家族人很不满,寻机报复。他的一个远房表弟也住在东马庄,这人给鬼子当特务,寡妇婆家人就向村干部检举说张志发来东马庄是跟表弟接头,村干部不敢隐瞒,如实上报县委。县里立刻派人将张志发抓走,未等查证清楚,大扫荡开始,县委向北撤退,于县长想带着他转移到后方再审查,但是杨书记不同意。
“那样不保险,万一半路脱逃怎么办?就地活埋吧。”
书记一句话,张志发就被拉出去活埋,战功累累的抗日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消息传到南关,张云亭既担心自己安危,又替胞兄委屈愤懑,一气之下真的投敌当了伪治安军。
队长被处决,指导员被审查,突击队群龙无首,自动解散。只存在了三个月的突击队,曾经名噪一时,令敌人闻风丧胆,这样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最终却毁于内斗,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突击队的溃散,仅仅是冀东抗日力量被内斗损耗的一个缩影,大敌当前,自乱阵脚的这场大清洗,对抗日力量的消耗不啻于敌人的进攻,更为严重的是动摇了群众团结抗日的信心。
县委撤到古北口,雨风奉命留守隐蔽。大扫荡开始,日军一边大屠杀一边进行宣传攻势,劝诱留守的抗日人员交出武器,如不“归顺”,则杀无赦。雨风被吓得魂飞魄散,这个抓捕“内奸”的能人勇士,毫不迟疑地交枪“归顺”,摇身一变成了丰润日军宪兵队的特务,为邀功请赏十分卖力地带领鬼子抓捕隐蔽在各村的抗日干部。
张达民虽然被八路队伍清理出来,在鬼子名单上仍然是罗文口村第一名的抗日分子,一围庄就得逃到别的村躲藏。鬼人在丰润县城至左家坞镇的公路上,沿途修建了三个炮楼。各村周围都挖了很深的沟壕,全村只留一个出口,还派了特务监管各村保长。这种情况下,围庄时很难逃脱,所以,他几乎不敢在家里居住。可是各村的村干部都知道他已经被抗日政府剔除,所以没人给他安排食宿,只能在破庙窝棚庄稼地里栖身,找到啥吃啥。有一次,竟然两天没吃上一口东西,饿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胃肠里胀满了气,顶到嗓子眼,嗳了几口后,又阵阵泛酸,不好意思乞讨,只好往回走,拖着软绵绵的双腿走到罗文口村头山坡,只觉心慌气短额头一层虚汗,看到老张干的小屋,进去就问:“有吃的吗?快给我点。”贫穷的老张干只有半盆剩下的高粱米饭,连块咸菜都没有,他就端着盆狼吞虎咽的吃个精光。
“唉,黑白颠倒,好赖不分。要不是为了乡亲们,我都不想干了。”老张干在木墩子上用力地磕着烟袋锅。
“别介,全村的性命都指望你这棵信号树,你不干了,鬼子最高兴。”达民劝解道。
“这道理我懂,就是心里憋屈。”
咔嚓一声,烟袋杆断了。老张干恨恨地骂了句脏话。
下一餐在哪里?明天怎么办?达民茫然地站在山坡上,满天乌云堆积、田野绿浪滚滚、村庄里狼奔豕突,陷入绝境的他走投无路。
作者简介:业余写手。冀东人。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3 小路(三十 )
- 浏览:52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1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6 樱花树下
- 浏览:46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3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39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290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8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35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7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89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4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49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4 换妻
- 浏览:16247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2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