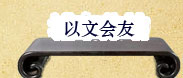孤独的梦 
在他眼里,天花板显得很高。几处曾渗水的湮迹,似乎由不知名的手绘成几幅图画。一片象澳大利亚的地图,整个国家天然地被海水包围着。有一片象法国路易王朝时戴着三角帽的军官头像,墙面上一道细细的裂纹恰好在尖鼻子下方,犹如一道胡须,看上去其表情象是在嘲笑谁。还有一块象缩成一团的猫和一头卧倒的牛,只是猫很大,牛却很小,只有猫的五分之一。
他很想动一下,但力不从心。一年多了,自中风后就只有瘫在床上,能吃能喝能想,就是不能动。
那不是扑克牌么,他看见茶几下的一副扑克,上面已落满一层厚厚的灰尘。用一副扑克牌玩接龙不太容易,因此号称“过五关斩六将”。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彻底失去工作,交街道居委会管制,十多年来就一直用它“过五关斩六将”。没人与他说话,没人。有时,他默默地瞧着窗外,瞧着巷子里疯闹的孩童,突如其来地冒出想和他们一起玩牌的想法。于是,他轻轻地喊:“来呀,上来玩牌呀!”孩童们抬起头,却从二楼小窗口中看到一个怪异的老头。他想努力地笑笑,但长期的郁郁寡欢使面部肌肉显得僵硬,反而使他的面容变得可怕。孩童们惊恐地望着他,终于一跑而散。这时,他往往长叹一口气,定定地望着牌中的“王后”和“武士”,心中想着他的孙子和外孙。他们要能回来多好啊!
自老伴患病远去云南小女儿家疗养,他就一直盼着周末,到那时住在长江对岸的外孙就会来看他,这是老伴安排好了的。那是一个早熟而懂事的孩子,虽只有上十岁,与老年人倒也可以对话,每次来除了带些吃的,还会带来好多外面的消息。他对这个外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耐心和慈祥,终于有一次他不厌其祥地把“过五关斩六将”的玩法教给了外孙,并且送给他一副新的扑克牌。
“给我吗?”孩子望着他。
“送给你。”他郑重其事地说。一点也没有长辈对下辈的那种“恩赐”或娇宠意味,而是一种很平等的赠与。孩子因为得到老人的尊重而高兴,尽力做出大人的样子。当他看到外孙用他的扑克按他的游戏方法贯通接龙,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可现在没法玩了,牌躺在盒子里,没了人气,也就没了生命。
他似乎又听到一阵强大的管乐声,这首旋律的歌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道旋律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他记起他在屋里忙碌着,垫着凳子从墙上摘下吴昌硕的山水与何绍基的书法字,环顾四周却无处可藏,只得塞在柜子和墙的夹缝中间。“扫四旧”就是扫荡传统的一切,他有经验,运动排山倒海般涌来时是无可逃遁的。他的家也是注定要抄的,还不如把“四旧”物品统统拿出来,一览无余地放在客厅,免得到时候翻箱倒柜弄得难以收拾。明清时的瓷器、古玩,一些名贵的字画、书籍等等,堆在小房的一角,老伴将字画的画轴拆了下来,竟装了一桶。他问:“你拆这干什么?”老伴苦笑地答道:“做杆面杖总可以吧。”他不作声了,这也是精神变物质?可能是他不属于任何单位,没有人想起他,所以“红卫兵”们到底没有来。但事情并不算完,街道居委会和邻居倒三番五次地跑来看顾,这些个顶着“红五类”招牌的小商小贩们先是啧啧称道:“你家的好东西还不少呢!”继而指着那些古玩字画冷笑连声:“哼!哼!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感到好笑,却笑不出,否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说:我上交,你们拿去吧。居委会的积极分子眼中闪烁出贪婪的光,她拿起一个明代的笔洗缸嘲弄地说:“这盛饭也不方便嘛。”但是,以红色居委会的名义他们拿走了那些“四旧”,处理的方法绝对是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成了炸油条的煤球炉的引火之物,另一部分由于进了碗柜也许有幸保存至今,只不过笔洗成了汤碗,笔筒成了筷子筒。不过,他毕竟躲过了一劫。
远处似乎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急促、热烈,给人一种警醒和振奋的感觉。他有种亲切感,几十年的铁路生涯都是在列车的轰鸣声中度过的。当年他从铁路学校毕业,从实习生到站长、段长直至京广线郑州以南的总调度长,历经风风雨雨,万没想到解放后被打入另册。他感到莫大的冤屈和不服,铁路部门是国有企业,他不过是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级职员而已,怎么能把他和那些他一向鄙视的政府中的政客相提并论呢?他在企业属于打工的,到头来政治地位竟还不如一个资本家!是的,脾气是不好,谁都敢顶,那是因为铁路专业管理方面他是权威,而铁路就崇尚权威,哪道车也不能乱跑。在交通枢纽上,任何一个局部的失误都会导致运输的混乱和交通的梗阻,严重的就是车毁人亡。他遵从西方严谨的路风传统,而深恶痛绝毫无原则的灵活性。然而他却没有明白,你顶国民党的官僚可以,你能顶共产党的干部吗?在专业管理上的固执己见,终于使他“享受”了政治审查的待遇。不到一个月,上级有关部门公布他的“历史罪状”,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桂冠”,使他永远告别铁路,成为被“管制”对象。他再也不能领略火车有节奏的远去声,而只是永远承受那车头沉重的到站喘息。他沉沉地喘了一口气……
“砰!”“砰!砰!”外面传来枪响。他有些惊诧,外孙告诉他,这是造反派相互间的武斗或是玩枪。他不理解的是,既是文化革命,怎么要动刀动枪呢?共产党比国民党要好,国民党就是动不动拿出枪来吓唬人的。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抗战初期的一幕。他那时是汉口车务段的段长,主管车皮的调配和车站的物资运输。他开完调拨会,刚进自己办公室的门,只见一个国民党军官从椅上站起来,趾高气扬地问道:“你就是段长吗?”
他扫了军官一眼,不快地问:“有何贵干?”
“给我调两个车皮,明早发长沙。”军官大大咧咧地说。
“你要车皮干什么?”他极为厌恶那些假公济私的军政官僚,看得出来这个家伙根本就不懂铁路程序。
“他妈的,这是军事秘密。有你知道的份?”军官虚张声势地说。
“没有!”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没有车皮!”他清楚地重复了一遍,对军官傲然而视。
“我告诉你,这是抗战期间,耽误了军事行动,要你的命!”军官气势汹汹地说。
“对,现在是抗战期间,往北方的车皮都供不应求,极度缺乏,你往南运什么?前线在哪里?”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快跟我发车,不然老子崩了你!”军官威吓地拔出手枪。
他何时受过如此胁迫和污辱,不由目眦俱裂,大吼一声:“兵痞!”军官果然朝天开了一枪,“砰!”的一声异常响亮。几个员工见势不对,突然冲上去,缴了他的械。军官哇哇大叫,声称要到上面去告他,他却气愤不已地叫道:“我还要告你呢!”这件事果然闹大了,通过铁道部竟然惊动了最高当局,最后追查下来方知那家伙是某集团军的一个上校团长,当时与上级沆瀣一气发了一笔国难财,于是想以军用物资的名义转运回家乡,他以为凭一身“老虎皮”就可通行无阻,没想栽在铁路上了。
后来,为了保证铁路系统不受各种势力特别是个别军队势力的干扰而直属当局调派,上面居然发下指令授予铁路站长以上的各级管理人员以军衔。他后位居区域调度长,所以授衔为少将。尽管他对此并无兴趣,作为一个高级技术管理人员甚至觉得与军政沾边有种不干净的感觉,但毕竟给工作带来了方便,谁敢在将军面前发威呢?
然而,福祸相依,这个“少将”的头衔,却给他的后半辈子带来了巨大的不幸。逻辑非常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国民党的“将军”自然就是天然的“反革命”了。他无论怎样向有关部门解释申辩都无济于事,派出所的一位户籍警说:“戴‘帽子’这是对你的宽大了,因为你没有血债,否则早就枪毙了。老老实实呆着吧。”他欲哭无泪……失去工作意味着断绝生活来源,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儿女们大了,他们自食其力都在为政府做事,资助一点就可以凑合。离开自己的专业才是真正的痛苦,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在站台上不舍地徘徊……
仍然是枪声,一片枪声。1938年10月25日,气压低得空气中可以攥出水来,日军都城联队攻陷汉口。整个铁路系统置于三八大盖的刺刀监视之下,日本人为了长治久安对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倒有几分“客气”,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种屈辱的现实: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侵略者服务!他暗地里联络了几个胆大的同仁,发誓不为日本人做事,决然离开铁路,消失在茫茫大武汉之中。
这是第一次离开他的岗位和专业,但这也是他的骄傲,是他人生值得一书的重大一笔。生活却是无情的,尽管住在法租界,没有收入体面的生活是难以维持的。厨师辞退了,车夫辞退了,夫人由太太变成家庭保姆,可一家十来口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他变卖家中的一切,最后只得靠着自己对文物的爱好和鉴赏力摆起地摊,只是那地摊离家很远很远,不能见熟人,不能见家人,不堪回首……
下雨了,他听见雨水打在屋檐打在窗子上的声音。屋子里黑洞洞的,他想叫外孙开灯,又觉得开灯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在黑暗中回忆往事来得安静。……那是一天傍晚,也是一个下雨天。天井里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家人面面相觑,这兵荒马乱之际谁敢开门呀。他走到门边,问道:“谁?”
“快开门,日本人在追我!”门缝中传来焦急的声音。
他打开门,一个穿黑色长衫的人闪了进来。此人约莫三十七、八岁的年纪,神情机警而精悍,向他抱拳道:“先生,打搅了,能让我躲一下吗?”
他想了想,说:“你跟我来。”说着将他引向内室,指着一个古老的柏木大衣柜,示意那人进去。那人点点头,钻了进去。
过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敲门,这次来的是日本人。一个翻译模样的人问:“有生人来过吗?”
他神色自若地答:“没有。”翻译官在他的几间房转了一圈,出来对为首的日本军官嘀咕了几句,他以他早年学过的日语听出了大概意思:这是家有身份的人家,多半不会与新四军有勾结。咱们再到前面去找。
正在这时,他四岁的小女儿从内室出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大柜子……”他顿时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一步迈到女儿前狠狠一巴掌,口中骂道:“要撒尿到厕所去,到处乱跑什么!”女儿大哭起来,夫人一把将她抱进了房。所幸日本人和翻译都没听清什么,日本军官厌烦的一挥手,他们走了。
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又过了半个时辰才请那年轻人出来,并请他饱饱地吃了一顿。临行时,那人握着他的手诚挚地说:“大恩不言谢。我们不会忘记你的。”他难得的露出一丝笑容:“哪里,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
当天晚上,他抚着小女儿红肿的半边脸颊,心中发出一声长叹。十几年后,当他被戴“帽子”时,老伴向他提及要不要去找一下那个“新四军”,他恼火地训斥道:“难道我是图回报的人吗?真是妇人之见!”
啊,怎么这么亮?外孙进来拿东西,每次他都要在他床边来看看他。他对外孙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打败日本人很热闹哇。1945年8月,日军投降,沦为日伪政权统治达七年之久的武汉终于光复了。在一片舞龙船的游行中,铁路局把他请回去了。近七年的漂泊,使他见到同事们很有一种沧桑感,同事们更尊重他了。他重操旧业,得心应手,又恢复了往日的尊严。1947年2月,上峰有令专列运石头,直发河南郑州以北。他知道这是花园口的黄河堵复工程。1938年6月时,日军侵占开封,逼近郑州,国民党军队不战即溃,为阻止日军的攻势,竟不顾后果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顿时河水泛滥,豫东、皖北、苏北一片泽国,大片土地形成盐碱地和沼泽,“黄泛区”在祖国苦难的大地上又留下了一片创伤。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他气得捶桌子,在家大骂国民党军队无能政府腐败,却无可奈何。
这次堵复工程,他倾注了热情,一丝不苟,运筹帷幄,调度有方,给工程以有力的支持。47年3月,决口堵复完成,黄河水复回故道。他自认为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并受到当局的嘉奖。没想到这个“嘉奖”后来也是他的一条“罪状”,因为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的“嘉奖”,肯定是反动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嘛。历史在开玩笑,人们却被玩笑所蹂躏。其实谁会把那些身外之物当回事呢?要对的起的是自己的良心。这才是为人之本啊。
改朝换代总有它的道理。自推翻满清以来,兵连祸结,战乱不断。旧中国是腐败肮脏的,每一个正直的人都迫切地盼望改变现状,他又何尝不是做着这样的梦。这下好了,风卷红旗过大关,共产党将统一全中国,从此再没有租界,再也不用做二等公民,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孩子们是最敏感最激进的,他们给这个传统的老式家庭带来新鲜空气。大儿子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临走时才回家打招呼。全家人又是惶惑又是激动,不知如何是好。他开明地说:孩子们,你们都大了,我不阻拦你们,去迎接新世界吧。大女儿、二女儿进了革命大学,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小女儿最有意思,报名参军因年纪不够被部队送回,后来部队带兵的人被其执着精神所感动,终于使她如愿以偿。只有最小的儿子按步就班进入了医学的专业领域,在兄弟姐妹中成为一个真正与父亲一样的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他很为自己的儿女们自豪,并认为自己是有眼光的,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大势,这种自信使他沉醉在最大限度的满足之中。他在黑暗中笑了,旧社会过来的旧职员,谁能象他这样呢?当然,他不会料到,自己会戴上一顶“帽子”,而这顶“帽子”却给他的儿女们留下了永远都挥之不去的阴影。大儿子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调往新疆阿克苏,不过不是搞他钻研的国防科技中的保密项目,而是去了地地道道的建设兵团。大女儿被单位中人歧视,以致落下终日惊恐的病根。二女儿从省委调到一所小学。小女儿提前退伍。小儿子虽医道娴熟,却从来不被重用。在当前的这场“文化革命”中他们更是日子难过。这都是我的“罪孽”呀,他的心在梦魇般的重压下痛苦着,一时竟老泪纵横,难以自己……在月光下,他泪眼婆娑地瞥见书桌和衣柜下的一堆手稿,那是他编写的65-66年的“年鉴”。终日的寂寞使他产生想做点什么的想法。坐在家里能做什么呢?歌颂我们的新社会歌颂党。他诚挚的想,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是她把历史推向前进了。我的委屈不算什么,那是有关部门搞错了。我要编年鉴把共产党的丰功伟绩都记录下来,这样才能实现我的价值。他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长江日报》,以为只要忠实地记录下报纸上的新闻就可以编撰出《年鉴》并可以出版,他不知道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三十年代。他不停地抄啊写啊抄啊……默默地干了两年。快编完了,人却不能动弹了,他又一次感到心痛,有一种大业未竟的伤心……
天花板上好象出现了新的湮迹,象一只老山羊。每下一次雨就会有新的图案。这只老山羊就是我,我属羊,一只带角的羊。他想着,这一生哪,也没做什么事,不过就象山羊一样清廉一些,耿直一些罢了。七十几年了在这世上没轻松过,我累了,疲乏了,该走了。他慢慢闭上眼睛,猛然听见老伴的哭声和外孙的呼唤,老伴哭道:“你等一下,等孩子们来了再走!”是呀,一个孩子也不在身边,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们了,真想他们啊……算了,不见他们也是对他们好啊,他们有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父亲……他紧闭的眼角悄悄滚出一颗泪珠。
他孤独地向前走着,只觉得四周为一团白雾笼罩,哪里是路呢?世上本没有路哇……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4 小路(三十 )
- 浏览:53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2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8 樱花树下
- 浏览:47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1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308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9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3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9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1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5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53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6 换妻
- 浏览:16248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