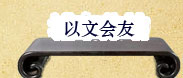迷雾在晌午消散 
双眼井村坐落在起伏的丘陵一带,几十户人家几乎围着两口大井。村子起初并不是这么叫唤的,是从村民打出两口大井才取了这好听的名儿。其实这村子别的倒不怎么有讲究,最是讲究和最让人称道的是,这村里的年轻小伙当兵的最多。就在前几年采摘包谷的秋上,这村的村支书的二儿子就报名参军去了。当送兵的锣鼓鞭炮热烈响过之后,人们才将这村庄的名字,在空闲的时候多念叨几次。
深秋的寒风刮过了丘陵,像一把漫天的高粱扫帚,拂过双眼井村的一片土地,透露出一片清冷。
村庄的夜空黑压压一片,就像被一块无形的黑布包裹着。窄窄而弯拐的土道上,清清凉凉寂寂冷冷的,几乎听不到有什么动静发生。几只野狗从巷道里冷不丁地窜出来,惊得旁边树上的宿鸟发出慌乱的叫声。然而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恢复了山岭岩石一般的沉寂,让人似乎觉察不到村庄的一丝活气。
大井一个人闷闷地走在巷道上,闷闷地抽着呛口的烟卷。他要在今夜将村里的旮旮旯旯,都实实在在走上一遭。因为明早的天色一发亮,他就要带全家人离开这生他养他三十多年的山村,去东北的佳木斯大城市讨生活了。大井并不是村里第一个去佳木斯的人,这几年来,顺子、来福、根生等都带着家人陆续去了佳木斯。听说他们的日子都过得比村里好得多,都还生了孩子。村子里的人几乎都走掉一半了,剩下的人家还在不停地犹豫徘徊。想起这些昔日滚成一团的伙计们,大井的眼泪便情不自禁地就滑落下来。到了眼下这个无可奈何的地步,他大井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坚持原来的观点了。
走出了巷口不远的时候,顺子反复劝说大井的话,再一次涌上他那翻腾的脑际。大井哥,咱们村的风水都破掉了,你就和我们一块走,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临去佳木斯之前,顺子曾一个劲地劝说大井。大井的头摇得像个拨郎鼓。也一个劲地驳斥着说,别听那些人喝高了瞎咧咧,好好的一个村子怎么风水说破就破了呢?那你倒是说说看,我和来福几家的孩子咋说没就没了呢?顺子说着说着眼里就含满了泪水,脸上挂满了无尽的忧伤。顺子他们打定主意走后不久,大井的孩子也是命中注定一般难逃劫难。想到这些令人不堪的情景,大井用力捶了几下自己的脑瓜,一把蹲地上呜呜哭了起来。
这村庄后面挨着一座不太高挑的山岭,岭上的石头也许多了长不出什么树木。村庄跟其他队部的村落是遥遥相望的,距县区城镇少说也得一百多里地。人生一世生老病死寻常事,平时村里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一般都去村南端找老中医孙老二。这孙老二年轻时曾在县城药店当过学徒,跟着一个老中医学了些本事。到了年纪叶落归根回到村里,开起了个一间房的中西药铺。虽不能说是华佗再世那么让人神奇,一般的小病小痛倒也能对付。而村里一些上岁数的人,孩子闹起啥子毛病了,往往去村北端找神婆麻嬷嬷。麻嬷嬷说有花甲了,独居在一所不大的旧屋里。谁的孩子吓着了,惊着了,没精气神的,村民自然而然想起了麻嬷嬷,就去找她跳跳大神,喊魂儿,孩子立马活蹦乱跳的了。
只不过,近几年村里孩子有了毛病,无论是找孙老二,还是找麻嬷嬷,却不怎么管用了。眼睁睁瞅着孩子们越来越没神采,到最后就没了气,顺子他们几家的孩子就这么莫名其妙没的。瞅着孩子们一个个莫名其妙死亡,村里的人心惶惶,六神无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村里绕着兜来转去。
就在某天的午间,村里的人刚刚吃完午饭。一个算命先生手擎一杆旗幡,上书“活诸葛”三个大字,摇着铃铛慢悠悠进了村里。村里平常光景很少见到算命先生,听得了外面传来的清脆铃铛声,村民不觉纷纷跑上前去,围在算命先生身旁,七嘴八舌叽里呱啦,求他好心指点指点迷津。算命先生停住脚步,拄着那只白布黑字旗幡,左手捻着羊尾胡须,微闭双眼嘴里不停念叨,一派神气十足的样子。
听完村民的一番哭诉,算命先生捻着胡须慢条斯理说,看来你们村里的风水被破了啊!村民听罢不觉一惊,焦急万分问道,大师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算命先生捋着胡须,环视了围着他的村民说,进村我见你们村前有个大口井,好像你们村后面也有一个吧?心直口快的亮子的娘说道,可不是咋地?这两个大井是搞兴修水利那会,是我们不分日夜打来的,能浇好几百亩地,可稀罕宝贵着咧。
算命先生朝上微微昂着脑瓜,微微闭着双眼,不紧不慢地说,能浇地自然是宗好事,可好好的风水就被破坏了啊!这卦书可明明白白写着村前村后井接井,村里少儿皆短命啊。大师,那有什么破解的法子吗?亮子的娘不觉挪动了身子,有些着急地追问起来。有倒是有…...算命先生边说边放出眼色环视众人。亮子的娘会意地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块钱,递了过去。算命先生伸手挡住了她递过来的手,继续沉默不语。亮子的娘见此又转回家去拿了十多斤豆子,一把递给了算命先生。他叹息了一声摇摇头,把装着十多斤豆子的袋子,慢慢放在了自己身旁。然后,他继续微闭着眼睛捻着胡须不说话。
旁边的村民见到这个情景,一个个从身上掏出仅有的零票子,或者也回家去拿些物品,放在算命先生的面前。他显得有些高兴,脸上露出了微笑。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拿着那把桃木宝剑,挑着一块黄色绢布,兜着八卦步子舞了好一阵。停下来后,算命先生吐了口气,对村民说道,看在大家一番善心的份上,我已使出了看家功夫,近期该不会再犯事儿。不过,要想永保平安,最好还是把那两口井填上为妙!说罢,算命先生向村民双手合十,朝前方绕圈儿拱了一拱。然后,收拾好家什走了。
村民纷纷找到村支书家里,吵吵嚷嚷闹着要填那两口井。什么?要把那两口井都填上?村支书大井爹魏老栓听说要填井,顿时火冒三丈,满腹愤懑。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正是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才打了这两口井。这两口井让我们多打了多少粮食啊!你们现在仅凭一个算命的瞎咧咧,就想把它填得不见尸骨?你们拍拍胸口想想,真得狠得下心来做这败家子的事?
有几个不太年轻的婆娘,一把眼泪一把口水地说,打粮多有啥子用啊?眼瞅着孩子们一个个的没了,没个后人接续香火,还算什么生活兴旺家族和美啊?魏老栓的眼瞪得像个铜铃,扯开嘴巴大声叫嚷着,孩子没了,是有原因,咋跟水井扯得上?肯定另外找原因,听人瞎咧咧想填井,没门儿!
说来也是怪了,就在魏老栓拒绝填井没多少日子,大井的小儿子忽然一下病了。这孩子得病后软不耷拉,一天难吃一口饭,就像掉了魂一样。大井娘带着孩子去找王嫲嫲叫了魂,可一点作用都没有。接着,大井媳妇又领着孩子找了孙老二,好几服汤药喂下去,也没见什么好的动静。眼见得那孩子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半夜里竟然没了气儿。在那天夜里,大井媳妇哭到天亮,眼睛肿的像烂桃子。
眼见得宝贝孙子一下没了,魏老栓整个地失魂落魄,人都矮了一大截。在家人的一片埋怨声中,他把放在猪栏里的半瓶农药,拿出来掺在一杯酒中饮下,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 大井的心碎成了两半,彻底地失望透顶。他横下心来决定要离开,想赶在天亮之前离开村里头。
然而,当大井收拾东西准备带一家老小出发时,大井娘却说啥也不肯走。大井娘说,我们都走了,二井回来咋办?我还要给他说媳妇,成家立业呀。想起在部队当兵的二儿子,大井娘哭得嗓门儿都嘶哑了。那你一个老人住在老宅里,我又怎么放得下心呢?大井耷拉着脑瓜,哭丧着声音劝说道。
放心吧,儿子。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结实,我要等着二井回来呢。大井红着眼圈沙哑着声音说,等我到那边闯荡了两三年,就一定回来接您过去住。悲悲戚戚说罢,母子俩相互一把搂抱着哭喊起来。哭够了,大井终于打点行装,带着媳妇和8岁的女儿,带着对故乡的依依不舍,到佳木斯谋生了。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白驹过隙,弹指三年过去了,二井从部队退伍归来。自从老支书魏老栓走后,村里的领导班子徒有虚名,公社安排二满叔代理支书,可他只是答应着,从没具体管过事儿,整个村子终日笼罩在一片死气沉沉中。公社洪书记愁的夜不能寐,却又徒叹无可奈何。这么偏僻的一个小村子,总不至于专门派个村干部去吧?再者说了,谁又愿意自找苦恼去那个寒酸伶仃的村子呢?
二井回家那天去公社武装部办手续,当洪书记知道他是老支书魏老栓儿子时,不禁眼前一亮。何不让这小子挑起这大梁呢?明天我就向县里汇报。洪书记心里暗暗盘算,决定使出最后的招数。
二井走马上任了。他的任命的形式很简单,但村民们后来得知后,对他还是一致认可的,毕竟人家在部队里闯荡过见过场面。二井当了支书发扬了部队的作风,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他没有料到自己离开家乡3年了,家乡的面貌几乎没啥开眼的变化。自己担上村干部的责任,就必须要一头深入村民的家里头。他把村子挨家挨户上门走了个遍,发现像娘这样的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心里十分沉重。难道这个村子真的有问题吗?难道真的是那两眼大井坏了风水?到了半夜里,二井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感觉问题并没那么简单,这个世上哪有什么风水?所谓的风水先生都是骗人的把戏。对了,是不是村里的饮用水源出了问题?想到这里,二井再无心思睡觉了,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二井总算把村支部一干人召集起来,一起开了个特别会议。当大伙听二井怀疑水源有问题时,一个个把头反复摇来摇去。水能有什么问题啊?都是从大口井里冒出的水,我们几辈子人都喝这个水也没见有事儿!是啊,是呀,我们喝了不是也没啥事吗?这肯定不是水源的问题。
二井使劲拍响了方桌子,制止了众人的叫嚷,竖着身子朗声说道,也许孩子的身子骨扛不住呢?说什么我要取点样到县城里化验化验。二井找到一起退伍的战友陆宝国,前前后后说明了原因,并把随身带来的一壶水,掏出背包咚地一下墩在桌子上。陆宝国带二井找在县卫生局当传达的姨妈,帮忙找人化验水质。等了一个礼拜之后,出来的化验结果,让二井既是大失所望,又疑虑重重。那个化验的化验员传出话说,送来的检测样品,富含钾、钙、镁、铁等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完全无毒无害。
水源没找出所怀疑的问题,村里人更加怀疑是两口大井破了风水。就在这早不早晚不晚的时候,国华家的孩子又毫无征兆地病了,弄得村里更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又有几家嚷嚷着要去佳木斯了。 二井来到国华家里,看见他儿子小康静静地躺在床上,精神萎靡,似睡非睡。国华坐在旁边愁眉紧锁,不停地唉声叹气,小康他娘的脸上写满了悲哀,在一旁不停地抹着眼睛,哭得嗓子早没了音色。
忽然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瞪瞪的小康不由自主抽动了几下,又陷入了一片沉睡。二井见到这个情景不觉浑身一个激灵,猛然想起在部队发生的事情。当时军营伙房里老鼠特多,司务长买来鼠药毒杀老鼠,有些被药了半死的老鼠就这样一抽一抽的。当时他和战友们还逗那些可怜虫玩呢,莫不是…….
二井锁着眉头沉思了片刻,不觉抬头望着国华夫妇,你们用鼠药药过老鼠吗?家里都有养的猫,还用什么鼠药啊?再说咱们这里也没有买的,听说城里才有卖呢!国华媳妇擤了一把鼻涕,哭着说道。那小康最近都吃过什么稀罕物呢?我看还是带着小康去城里医院瞧瞧吧。二栓劝慰地对国华夫妇说。咱们山里的人,能有啥稀罕的吃啊?老中医孙老二说了,他治不好的病,去城里看也是白搭。再说了,城里又那么远,找什么地方住下呢?国华歪斜着脑瓜愁容满面,一个劲地吸着旱烟。这个朴实憨厚的山里汉子,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县城里呢。对于县城面貌的想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一般了。
小康娘忽然止住哭泣,轻轻嚷了一句道,小康说那天在大门口捡了两块糖吃了。看来这个糖里有文章!难道它是一种杀灭老鼠的糖?可村里并没搞过放药灭鼠啊。这一定是有人起歹心做的恶毒事,故意投放这个毒糖做诱饵,诱惑懵懂无知喜爱甜食的少儿,企图就是害得村民们断子绝孙,灭绝香火,达到不可告人的阴谋目的。琢磨到这里,二井猛然坚定了主意,说道,这次我还得必须走一趟。
村里的人家没几个小孩了,有孩子的都已经长得很大了,投放毒糖的人也可能按兵不动了,眨眼过了2个月居然出现了一片平静。世上的事最怕的是有心人,这一回二井的心是绷得紧紧的。这两个月里,他根本没怎么睡过安稳觉。不论白天或黑夜里,他都悄然无声潜藏在某处,一双眼睛纹丝不动盯着那些有小孩的人家。他的心血总算还没白费,终于在某天的黎明,发现一个披着黑衣驼着身子的人,匆匆溜到了村民张家财的家门口,冒冒失失做了个抛东西的动作,然后一溜烟朝北边窜走了。
带着那两颗从地上捡来的东西,二井又托求了陆保国姨妈的熟人。当这回独自去检测的结果,从二井的嘴里严正地说出来后,村里的人们都像听闻了一声惊雷,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们不得已接受了这个事实,孩子果真是中了慢性老鼠药的毒。二井将那化验员说过的知识,一一向村民们做了宣讲。
这种鼠药有一定的隐藏时间,发病时产生发热、呕吐、抽搐、食欲不振、呼吸困难。如果不及时进行催吐、洗胃等治疗,自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听了二井的一通宣讲,村民才像突然醒了酒一样。
张家财的孩子金锁得救了,其他家里的孩子也脱离了危险。村里的人似乎都大大松了口气,开始安安心心搞好劳动过日子。只有二井的心还不平静,眉头一点儿还没松,搁在心头的石头还在。二井在村里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得知被伤害的孩子的症状都和小康一样。二井的走访越走心情越是难受,心头被扣了一顶黑沉沉的大铁锅。作为受过部队教育的自己,怎么也得要彻底解决这个大问题。
走在村里弯弯拐拐的巷道上,望着宁静与平和的人家,二井不由得琢磨起来。既然村里的人都是养猫捉鼠,那么那种鼠药到底从何而来?他感到那黑衣人像个神秘的幽灵,时不时都在村子的角落里游荡。二井找到了村民兵连长潘昌林,给他布置了一个特别任务。布置任务的话语中,二井一再对他叮嘱,要沉得住气,不要轻易打草惊蛇。潘昌林对布置的任务很激动,自然是保证坚决执行照办。
不声不响过了几天,潘昌林跑到二井家里汇报。他带着民兵晚上在村里巡逻,发现地主崽子彭添仁很晚才从通往县城的道上回来。他的身上斜背着一个布袋,好像不怎么显得沉重,但不知里面究竟是什么。不错。继续监视他,下次定要抓他个现行!听完汇报,二井握住拳头,用力挥了一下。
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二井带领民兵连早早埋伏在村子北头。说是埋伏其实有点夸张,不过是大家伙都趴在村道的两旁不动。不知道过了多少袋烟的功夫,远远瞧见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勾着身子晃晃悠悠进了村里。站住!潘昌林跨步迎上前去大喊一声,黑影防不胜防,陡然间一个惊吓,哎吆叫了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二井当即打开手电筒一照,果然是彭添仁,在地上缩着身子打啰嗦。
快说,去干什么了?袋子里装的什么?民兵们一把围上来七嘴八舌问道。我…我…..彭添仁浑身不自主地抖动着,说话畏畏缩缩。到底干什么啦?再不说打断你的狗腿,就像当年打你老子一样!潘昌林高高举起了枪托,厉声地喝令着。啊啊,我说,我说,不要打我!彭添仁双腿扑通跪了下来,双手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子一般。老实交代!民兵们握着枪杆,紧紧地围在他的身旁,大声怒喝。
是是这样的,我爹的那条伤腿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难受,我去县城里给他抓药去了。彭添仁哆嗦着双手打开了身上的布袋,不安地望着民兵们说,你们看嘛。二井、潘昌林凑近袋口一看,伸手到包里轻轻捏了捏,估计得出是一包包的药。潘昌林灰黑着脸,目光炯炯地盯着彭添仁,发声问道,那你为啥每次去城里要早出晚归,还做出那副鬼样子?唉唉,我薅了些兔毛去城里卖了换钱,怕被你们看见了又说是搞小农经济,担心你们又会来整我一通。说来话长,去城里那药店抓药真不容易,买药看病的人排长队,来来回回搭车走路也费脚力。彭添仁低下头来做出解释,那声音小的像蚊子在叫。
二井板着脸出声地问道,那你为啥不找孙老二买药?二兄弟,你退伍才回来有所不知,咱们村有讲究,不让孙老二卖药给我们这些出身高的人。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好跑县城药店去买药。
彭添仁说完不觉抬起了头,将一副乞求的目光投向了二井,说出了心中隐藏的那份委屈。你在跟谁称兄道弟?潘昌林说着随意给了彭添仁一枪杆子。别打他了。二井一把拽住了潘昌林的臂膀,接着冲他使了个特别的眼色。潘昌林对站在一旁的几个民兵发出指令,袋子留下来,把人关到队部去!
夜色越来越来粘稠,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二井叉着腰站在村道上,分明瞧见眼前有一道光,越来越发明亮醒目,把他的心里映照得透亮透亮的。潘昌林他们扛着枪已转身回来了,二井环视了他们一轮后说,现在我们马上去孙老二的药铺。然后,他带着潘昌林和民兵们一起朝村南口跑去。
叫开了孙老二的房门后,二井当即跟他说明了要求。孙老二马上拉亮了两盏电灯,药铺里顿时明亮亮一片。二井潘昌林随孙老二的脚步,走到药铺里的那只方桌子旁,把带来的彭添仁的那只布袋子,郑重其事递到孙老二的手上,眼巴巴地瞅着他的一举一动,期盼能得到一个明确而肯定的答案。
孙老头摸出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把那些药品从袋子里一包包拿出来,摆放在桌子上,然后仔细而反复地检查着每一包药。当看完最后一包药时,他一下摘下了眼镜告诉说,这些药就是些普通的消炎镇痛药,没有什么老鼠的药。啥子? 没有老鼠药?你不会看错了吧?潘昌林听罢一下子蹦了起来,两眼瞪得像一对灯泡。其他的民兵也沮丧着脸,像泄了气的皮球。孙郎中,你得好好想想,你能打包票说这药里没鼠药?二井说啥也难以相信,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忍不住带了一些火气发问。
孙老二一下端正了身子,神色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据我多年从医所知,鼠药是有特别的药面的,用一种糖衣纸包裹着;同时还配有一种药水,用一个很小的瓶子装着。这样小的瓶子,身上哪个地方都能藏上好几瓶。对着大井他们说完后,孙老二随意地拍打了双手,把那些药放回了那只布袋子。
赶快去队部检查彭添仁的身上!二井猛然间恍然大悟,一挥手给民兵们发出指令。一行人马急行军一样赶到了队部,把关在杂屋间里的彭添仁,一把拽在宽敞的堂屋里,将他的浑身上下从头到脚翻了个遍。接着又把那间关闭他的杂屋间,旮旮旯旯里翻了好几遍,愣是没看见一丁点老鼠药影子。
真是撞到了活鬼了!潘昌林急得直挠头皮,一把转过身去,抓过墙角的枪朝彭添仁捅了几下子。二井忽然灵机一动,拍了大腿嚷道,也许他这次根本就没买老鼠药,咱们得到他家里进行搜查!
民兵们被大井和潘昌林带着,像一阵旋风直奔地主彭万福的宅子而去。彭万福不安地躺在那张古老的床上,忽然听到院里发出很大的声响,还以为是儿子跑回来了。他仿佛突然来了一股劲,连忙瘸着一条腿打开了房门,猛然瞧见一伙民兵们闯了进来。他吓得顿时哇呀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
潘潘连长,你们这是做啥子?彭万福在地上畏缩着身子,打着哆嗦问道。你个狗地主,今晚可要跟我老实交代!潘昌林横了横手中那把三八大盖。快说!你儿子买的毒鼠药藏到哪里去了?民兵们也放出声调喝令着。哪买过啥老老鼠药啊?我们家养了只大猫,天天指望它逮老鼠呢。彭万福带着哭腔一副委屈地说道。叫你死不老实!潘昌林单手握着枪朝他捅了一枪托,彭万福咬着牙受不住疼痛,发出“哎吆”一声叫唤。只见一只大猫从桌子下蹭地窜了出来,夹着尾巴朝屋外一溜烟地奔了出去。
给我翻!瞧着彭万福不老实交代,二井挥着拳下了指令。眼瞧着就到了下半夜,彭万福家的柜子箱子袋子,坛坛罐罐被民兵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看见什么鼠药的影子。把他也押到队部里去!二井心烦意乱,左顾右盼,不停地跺着一双脚板,昌林更是有些气急败坏,把一双拳头捏得嘎嘎响。
瞧着彭氏父子俩被关押了有3天了,可就是刨他们祖坟也不承认老鼠药的事。连日以来的白天黑夜,二井愁眉不展,满面乌云,兜着步子在堂屋里转来转去。他不停地暗自琢磨,难道这父子俩真的是被冤枉了?投毒放药的另有其人?二井猛然觉得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黑洞,黑得那么玄妙而深不可测。从队部往家的路上走,二井时不时揪着他的头发,寻思着那个黑洞的玄妙,百思不得其解。
奶奶的个巴拉子!老子们过得不舒坦,你们也休想过好日子!奶奶的个巴拉子!二井经过村民臧金良的房屋时,传来一阵难听的叫嚷声。二井不觉停下脚步疑惑间,亮子娘从一旁的门洞歪着身子走了过来。二井赶忙迎过去朝她问道,婶子,金良兄弟他这是咋的了?还能咋啦?整天就是那个熊样,喝上几两猫尿就不知东西南北了。保不住又想起啥伤心事了吧。说罢,亮子娘冲着臧金良家那边吐了口唾沫,露出一副恶心的神情叫道,酒颠子一个!婶子,我陪你走,你说给我听,我还不知道咧。
二井对臧金良的举止感到奇怪,他还是多少了解他这个人的。他记得小时候经常听爹说,臧金良家三辈子贫农,他父亲解放前曾参加过农会,打土豪,搞土改,非常积极,很出色。解放以后,还曾在村里当过干部问过事儿。臧金良由于根正苗红,出身很硬,被派去公社供销社里当上营业员。
二侄子,这些年你当兵在外不知道,臧金良如今可是倒霉了。在公社供销社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因为搞贪污被赶了回来。回来在生产队搞不好生产农活,工分挣得少得可怜。连老婆都不愿意再跟他,领着孩子跑到外村嫁人去了,他现在不又成了老光棍了吗。亮子娘一番话把二井从回忆里拉了回来。那他没有去再找个老婆?听二井这样奇怪地发问,亮子娘歪斜了眼神撇了撇嘴,接着话茬说道,就他这个熊样的,成天混日子一般,喝醉了老不醒,还不时赌个钱,哪个女的会跟他?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见了他,都躲的远远的呢!听了亮子娘的一番话,二井心里顿时感到一丝沉重,停住了脚步。
亮子娘还是朝前头走着,二井不由得依然跟了上去,冲着亮子娘问道,婶子,金良他不喝酒时是个啥样子的?不喝酒?亮子娘止住了步子停下来,回味了一下接着说,不喝酒他倒还像个人,见了人也笑呵呵的,还怪喜欢抱人家的小孩子。可大人们都不让孩子粘他的边。那一回,他拿了糖块给代销点家的小孩吃,被店老板媳妇夺过来扔了远远的。亮子娘说着说着摆了摆手突然轻轻叹了口气。
婶子你说啥,臧金良他还买糖块给小孩吃?二井听婶子说出这句话,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亮子娘下意识地摆了摆手,瞅了瞅二井说,我也是听他媳妇告诉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冤枉金良他。好多人家的婆姨都这么说过,臧金良他时常揣着糖果在身上,趁大人一不注意,就塞到小孩嘴里去。
当天的夜晚时分,家家户户沉浸于欢声笑语。事先经过一番摸底,臧金山今晚要去冯来宝家玩牌。他们一玩肯定会搞到大半夜,趁这好不容易落空的机会,二井潘昌林悄悄推开了他家的门。进得屋里一番寻找之后,从他床底下的纸箱里,找出了几瓶小塑料瓶装的药水,还有一包方形的红色糖块。
公安局的几个警察开车来了,臧金山被二井他们扭送到跟前。他埋下头缩着身子,被反背着双手坐在车里。村民们都跑出来站在村道上,看着警车远远消失。二栓感到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一个晨曦撒满村庄山陵的早上,二井缓缓走上村后面的那座小山。他静静地俯瞰着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心潮起伏不停,掀起了一层层激动的波纹。此刻的村庄还沉浸在温柔乡里,宛若一个恬静娴淑的少女,躺卧在周围的大好河山的怀抱。而村里的那两眼大口井,恰如少女美丽动人的眼睛。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4 小路(三十 )
- 浏览:53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2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7 樱花树下
- 浏览:47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0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297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9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1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8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0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4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50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5 换妻
- 浏览:16248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