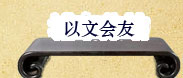七叔旧事(小说) 
一
七叔姓胡,是我的一个远房族叔,庄上人叫他老七,晚辈们都称他七叔。
七叔的妈妈一共生过八个儿子,到了晚年时,村里人都习惯叫她“八大妈”,我们这些孙辈都叫她八奶奶。八奶奶一生的最大遗憾就是没能生个女儿。
那时还是黑暗的旧社会,除了水旱灾害频仍,世道也不太平。到七叔成年时,弟兄八人中只剩下了老二老四和老七三个人。那年月,养儿育女都是广种薄收,难得的一半养得大。小时候听父亲说,其实他家的老六和老八也都已经长成了大人,只可惜老六在十七岁的那年替人家撑船,不明不白地病死在人家船上,老八被抓了壮丁,至今都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
我记事时,七叔的父亲就不在了,听说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个子特别高大,有一把蛮力气,一只手能将五六百斤重的碌碡扳得竖起来,五十多岁时得了大肚子病(血吸虫病)不治身亡。八奶奶的寿数还不算短,过到六十九岁。
村里人说,七叔长得极像他的父亲,高个,长脸,膀大腰圆。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脑瓜特聪明,没拜过师学过徒,靠自已瞎捉摸瞎摆弄,居然自学成才成了一个手艺不错的木匠。
我听他说过,他在十六岁的那年,曾央求他父亲让他跟表哥学木匠,他父亲不曾肯,父亲说:“学木匠要三年才能出师,哪有钱给你寻婆娘成家?”后来,他跟表哥要了一把上了锈的旧斧头和几样用得不能再用的旧锯子旧凿子,一有空闲就认真地打磨那些宝贝。接着,自己又仿制了一些简单的木工用具,他用了二十多年的角尺和墨斗(一种用来弹直线的器具)就是那时自己依样画葫芦鼓捣出来的。有了这些工具就开始练手,一开始是利用家中的一些零碎的木料制作小板凳,那种凳子在我们那里叫爬爬凳儿,要制作得四平八稳像模像样是挺不容易的,虽然只需要在一小块长方形的木板上装上四条腿,但传统的木匠是不用一根钉子的,全部是榫接。每一个榫眼都有不同的角度,不能有一点偏差。有一次,他的那个做木匠的表哥到他家有事,看到了他打的几张小凳,对他爸说:“这老七还真的心巧,我那个学了一年多的徒弟还打不出这样子来。”他爸说:“开始打的几张也没这么好看,后来他将你给我家打的那张凳拆下来仔细捉摸才打成这样的。现在,邻居们都将家中的碎料拿过来请他打,他有时候能捣腾到半夜。我现在倒是有点后悔没肯让他跟你学徒了。”表哥又说:“他脑子活,又有恒心,就是不学徒,将来也能会做一些荒木匠的活儿。”
表哥说的荒木匠就是农村常见的土木匠,那些人虽然不会制作高档的家具,但制作常用的桌椅厨柜和砌屋钉船这些粗木工活儿都不在话下。表哥也是一个荒木匠,而且还会做一些砌墙盖屋的瓦工活儿,在农村叫木瓦两作。后来,表哥还给了他一张用旧了的大锯,跟他说:“我那张大锯用了好多年了,架子坏了,你拿来整一下,把锯齿锉一遍,还能用。”七叔听了自然如获至宝,他正想要置办那样一张大锯。那时还不曾有机械轧板,破大料全靠人工拉大锯。他总不能老是用碎料打爬爬凳儿,大锯是木匠必不可少的一样工具。
七叔到了二十岁时,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木匠了。那年他娶了表哥家的一个小妹成了家。那时候表兄妹结婚不受限制,说是亲上加亲。听说,当年他们的这桩婚事还算得上是自由恋爱,因为他们既是亲戚,表哥又经常带着他替人家砌屋钉船,两个人日久生情,家里人也认可,这事就成了。
七婶是个典型贤妻良母,人长得也挺端庄秀气,惟一觉得与七叔不大般配的是个子太矮了点,大约只有一米五左右,跟七叔站在一起,怕有三十多公分的高差。不过,他们两口子好像特别恩爱,在后来的几十年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们生下了二男三女五个孩子,邻居们从来没见过他们扛过丧(扛丧是苏北方言,即吵嘴,)。
二
我是上世纪三年经济困难刚过时结的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因为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五个弟妹。一家三代十口人住在只有五六十平米的三间老屋里,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父亲就想替我另外搭两间简易房子,将我们这个小家庭分出去。那时都这样,结了婚的长房儿子就没资格再在大树底下乘凉了,他们都必须另立门户去为生计打拚。砌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市面上买不到任何建房材料,就是买得到也没钱,父亲因此一筹莫展。
有一天晚上,正好七叔和七婶在我家支磨磨麦(那时还不曾有加工粮食的粉碎机,我家有一副石磨),磨完后,父亲说:“老七,你别忙走,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讨讨主意。”
“你是想要搭房子将老大分出去?”七叔已经猜到父亲想说什么了。他接着说:“四哥哥,我看这事也不太难,俗话说‘船真屋假’,搭两间泥屋草舍花不了多少钱,你真想搭,我替你想主意。”父亲排行老四,比七叔大五岁,七叔都是叫他四哥哥。
“可我现在一样东西都没有。”
“你只要想办法买到一包水泥,我替你先预制两根水泥柱子,再买几根粗一些的撑船篙子就差不多能将舍子搭起来了。四面墙全用土墼(苏北地区的土坯,个头极大),只要有力气,不用花钱。盖屋的齐稻草也不难找。”
“听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大篙子供销社有得卖,就是怕没办法搞得到水泥,那东西上计划,要批条子。”
后来,还是七叔找公社里的李科长批了一包水泥,李科长那时在我们大队蹲点,家中女儿出嫁是七叔替他打的嫁妆。有了水泥,父亲又买回来几百斤黄砂,七叔只花了一个上午就将两根中柱浇筑好了。让人觉得挺神奇的是柱子里没放一根钢筋(那时也没处买),只放了两根毛竹片。七叔说“直柱顶千斤,没有钢筋也没事,如果要作桁条就非得用钢筋了。”柱子表面抹得十分光滑,腰身处还留了两处穿大梁膀子的榫眼。父亲感叹地对我说:“以前的木匠哪做过这些活儿,都是你七叔骨里巧,自己悟出来的。”
光有水泥柱子是做不了两副竖梁的,还必须有一些木材作梁膀子。七叔对父亲说:“我已经替你合计好了,你家门口河边上有一棵壳树,虽然那种树长得快,不结实,一般情况下不能做上房的材料,但现在没办法,我看也能凑乎着用十年八年,再说,那土屋也住不了多少年。”过了几天,父亲就和我将那棵平时只能作柴火的树砍了下来抬到七叔家里上大锯,七叔忙活了两天,居然用那两根水泥柱子串起了两副像模像样的竖梁。
后来,我在那所前后只花了三十多元钱搭起来的土屋里住了十多年,到上世纪七十代才拆掉重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七叔作为农村里的一个土木匠,凭着他特殊的手艺和别出心裁的创新为庄上人解决了不少难题。特别是一些要嫁女儿的人家,碰到没钱为女儿置办嫁妆时都会找七叔想办法,七叔总是不嫌其烦的将他们家里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旧柜橱整旧如新再刷上漆。让他们不花钱还能将女儿体面地嫁出去。他为人家做这些,一天只收一元钱工钱,碰到特别困难的人家还分文不收,只要管他几顿便饭。记得帮我家砌屋时,中午还是吃的掺了许多胡萝卜煮的饭。
除了这些,他在那个年代还有许多小发明。记得还替我制作过一个水泥大缸和一张特别笨重的水泥家神柜。虽然,那时市面上可以买到陶制的大缸,因为贵,买不起。制作一个水泥大缸只有一两元钱材料费,同样可以用来作茅缸或者用来储藏青饲料。制作过程又不难,只要在地上挖一个坑,在坑的四壁抹上水泥砂浆,隔几天就能将缸挖出来使用了。制作家神柜的过程就复杂得多了,先要用土墼在地上砌一个家神柜大小的内胆,然后在外面蒙上一层铁丝网,再在上面抹一层水泥砂浆,过几天再通过上面的出入口拆掉内胆,人钻进去将里面加一层水泥砂浆。七叔制作的水泥家神柜不但十分坚固耐用而且特别美观大方,在光滑的柜面上漆上油漆,画上假柜门假抽屉,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可惜这些奇葩的仿木家俱,后来随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结束,大都被废弃成了瓦砾。
三
七叔后来还当过三年生产队长,那些年,我在生产队当会计。
原来的那个队长因为嫖婆娘被人家男人捉奸在床,情急中,那人一扁担打断了他一条腿,被免了职的队长成了瘸子。打人的人是个富农的儿子,因此被判了一年劳改。七叔在队里人缘好,大家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
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但权力还真不小,就相当于一个二百多人口的大家庭里的家长。每一个劳力每一天干什么农活都要听队长支派,活儿有重有轻,那时吃不饱,都希望队长能安排轻巧一点的活儿。一天活儿干下来记多少工分也是队长说了算。要是队长要让哪个穿小鞋,那人只能天天干重活还拿不到大工分。能当生产队长的人大都是队里天不怕地不怕的狠角色,扛丧打架他随时奉陪,惹不起,只能忍气吞声。队里总会有几个促狭鬼,他们为了能沾到一点光,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奉承拍马,甚至还有人宁愿戴绿帽子默许自己的婆娘去勾引队长。
原来的那个队长是个色鬼,据说队里有三四个婆娘跟他有那种关系。七叔接任队时,队里就有人议论说:“老七正派,办事公正,当队长再好没得,就是太仁义了,怕治不住队里的那几个‘邪头’,”还说:“他虽然是个君子,平时跟妇女连一句玩笑话都没有,但他也不过才四十岁,可能当了队长后也难免会英雄难过美人关。”
幸好,队里的那几个“邪头”并没让七叔为难,他们看到七叔天天与社员一起风里雨来去,跟原来那个甩手掌柜大不一样,对待队里的每一个劳力都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家心服口服,后来和他都成了朋友。不过,说到英雄难过美人关,七叔还真的经受了一番考验。
队里有两个在那方面特别大方的婆娘,以前是队长的老相好,常常因为投怀送抱得到队长的照顾。现在“靠山”倒了,她们就打起了七叔的主意。其中有一个婆娘还是七叔的邻居,比七叔小两三岁,叫巧娣。巧娣是个高个子女人,可惜嫁了个武大郎似的丈夫,两个人站在一起女的比男的还要高一些。在七叔还没当上队长时,那婆娘就对他垂涎三尺,特别嫉妒七嫂那样一个矮小的女人竟然有一个气宇轩昂的丈夫。村里有个民办教师曾经跟巧娣开过一回文绉绉的玩笑,说:“月老真是牵错了红线,要是你家男将跟老七调换一下,两家不是就都般配了吗?”她听了一点儿也没生气,反而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这就叫‘一块馒头搭一块糕’。”
有一次,几个婆娘在场头队屋里拣稻种,我正好在隔壁的另一间里有事。听到她们说说笑笑,说的都是关于七叔的荤话,我就留意听了会儿。
先是巧娣说:“你们知道老七那玩意儿有多大吗?”
有人搭腔说:“你跟他家门靠门,怕是被他弄过的,说给我们听听。”
“有一次他坐在露天茅缸上解手,我看到那家伙挂在缸边上像个黄鼠狼!”
一阵轰笑过后,有人说:“怕的是把你馋死了,骚水淌了一裤裆?”
后来,她们又将话题转到七婶身上。还是巧娣先开的头,她说:“也真有点想不通,他婆娘那么个娇小人儿,怎么经得住的?看起来,七嫂子还整天乐呵的也不像是处在水深火热中?”接下来大家就围绕着这个话题讨论开了,她们越说越下流,我越听越觉得不堪入耳。只好故意大声地干咳了一声,那边顿时噤若寒蝉。过了会儿,巧娣在那边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
那时候,当队长的在这方面都是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很难有人独善其身。七叔的情况更特殊,有人不但想攀上他能得到一些小恩小惠,而且那些人还将他视为梦中情人。不过,好像七叔还真的一次没有失过身。旁的生产队的几个队长常常拿他取笑,说他是个“死人”,还有人说:“这队长让你白当了,爹妈给你一杆枪,枪枪打在老地方,你不觉得冤吗?”他回人家说:“寃什么,我有婆娘有儿女,还有打光棍的一辈子没碰过女人呢。人家当社员的那么苦,我们还去算计人家婆娘,这畜生事我不忍心做。”
四
七叔当队长的那几年,队里年年增产,工分单价也由原先每分工四分钱提高到六分多,大多数社员到了年终分红时都能分到一点现金。可惜,好景不长,七叔在四十三岁的那年冬天,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开始只是老是在清晨时觉得头疼,后来人也一天天地消瘦,还常常有不明原因的呕吐。到县医院一查,不得了,说是脑子里长了个瘤,而且很可能是恶性的。村里以前不曾有人得过这病,都说怕的是他平时用脑过度所致。
医生说,这种病只有到大医院通过手术切除颅内肿瘤,再配合使用其它的医疗手段才能有希望治得好。七叔听了,就知道他是得的绝症,恐怕是没救了。那时候,农村中没见过头脑内长了东西也能开刀,再说,哪来那么多钱?
那年,七叔家里有五个孩子,除七叔和七婶两个人拿工分,没上过一天学的大女儿只能算是半劳力,挣不了多少工分,还有两个儿子在上小学,最小的女儿才两岁。十二岁的二女儿平时在家煮饭带小妹子。因为粮食不够吃,每年分到的一点钱大部分都用来买副食品,经济情况还不如以前做木匠时宽裕。有一回七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在我跟前诉苦,说:“你七叔真不该当这干部,以前做木工活儿,人家管三顿饭,好歹都有两样菜,活儿也没这么重,还能挣点钱。他现在倒好,天天起早带晚地忙活,白天还要跟人家大劳力一起干重活。人家当队长才像个当干部的样子,平时站在田岸上指手划脚的,身上连个泥点子都没有。我看他这病就是累出来的。”
虽然那时看病没现在这么贵,但七叔这病没有上千元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按理说,碰到这情况,生产队里是应该扶持一把的,但那时的生产队还真的无能为力。生产队的收入和开支几乎全是非现金结算,公社分配的化肥、农药、柴油等计划物资,都是由我拿着分配的通知到信用社办贷款。队里出售粮、棉等农产品也拿不到现金,都是由粮管所、供销社开转帐支票到信用社。我这个当会计的平时手头只有很少的一点现金用于生产急需。再说,生产队在信用社帐户上也没多少钱,那时一斤稻谷国家的统购价只有八九分钱,一年下来能余下几千元钱给社员分红就不错了,怎么能批到上千元给人看病,莫说是个生产队长,就是大队支书得了这病,也只能听天留命。
七叔病倒后,先由我代理了个把月的队长,后来就从外队里调了个队长过来。七叔就这样在家里耗着。除了头疼,饭量还不小,就是没什么好东西吃。
一转眼就到了农历的春节。七叔有个嫁在上海郊区的侄女专程回来看他,那边的经济条件比这边好得多,说她们村里也有个人得了这种病,后来在上海一家大医院里开刀,总共花去一千多元钱,现在已经治好了。听她这一说,家里七凑八凑地借了二百多元钱,准备由侄女儿带他去上海。临走的那天,村里支书又找公社领导批了张条子,让我到信用社借了二百元贷款送到他家。
十多天后,从上海那边传来消息说,七叔已经在上海的一家最大的医院里做过了开颅手术,成功地摘除了肿瘤。还听说手术是采用的针剌麻醉,当时这项技术是我国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一桩发明,据说正在上海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夫人还参观了手术过程。真想不到,他得了这病,还让他见到了大洋彼岸的总统夫人。
后来,没过多少天,七叔和七婶就被他侄女儿送了回来。在他家,我看到了倚靠在床头的七叔,头上裹着绷带,面色还好,就是眼神有点怪怪的,说话也不着边际答非所问,我猜想可能是是刚做过手术,大脑思维能力受到影响。听他侄女说,他们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没办法,他侄女儿贴进去五百多元后,又欠下了医院八百多元药费,医院天天催费不肯发药,他们只能逃。
后来,支书关照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他送去一些消炎止痛的药片,让他将药费先记在帐上。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正半坐半躺在床头吃生胡萝卜。那天他神志挺清醒(听说这些天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告诉我说:“中午吃的粥,你七婶上工前洗了几条胡萝卜放在铺边上让我饿了时吃点儿。”他肠胃里没病,只可惜那时太困难了,饭粥都不周全,哪还谈得上什么营养不营养。第二天,我给了七婶五元钱,七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那年春天,七叔病情突然加重,饮食越来越少,人也像个傻子。没过几天就走了。
那时还不曾实行火葬,我请人将队里的一副旧水车拆下来打了一副薄皮棺材,打发他上了路。送葬的那天,七婶哭得死去活来,大家也陪着她流了许多眼泪。
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四十多个春秋,但村里的老人们还常常在一起谈起七叔的那些旧事。都说他是个好人,要是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或许还能多活好些年。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4 小路(三十 )
- 浏览:53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2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7 樱花树下
- 浏览:47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0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298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9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2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9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1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4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51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5 换妻
- 浏览:16248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