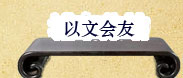下台的日子 
光秃秃的山丘环绕着的十里矿区里,一座座厂矿和一片片村庄星罗密布般地交织在一起。矿区内特别是公路两侧,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计其数的煤场。矿区的上空,时常被漂浮着煤尘的干燥的空气笼罩着。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以煤炭和电力生产为主的北山能源公司,就分布在这里。
时间悄无声息的把人们带到了2006年。支河恩似乎预感到,这一年,对他来说决不是平凡的一年。一则这是公司由市下放到县实行属地管理后的第一个年头,还不知道县里会对公司有什么样的改革举措呢。他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像以前的县属企业那样,一个个都给私有化了呢。二则时年50岁的他,知道自己在位的年限不长了。因为以前公司归市里管理的时候,市主管部门曾经按52岁“一刀切”的办法,调整过公司班子。虽说现在公司的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最多再干上两年,到时候就是上边让干,也就不能干了,不然无法向以前已经按这个年龄退下去的原班子成员交代。因为他是一把手,不能别人按这个年龄执行,轮到自己就另当别论,那样岂不让人耻笑。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样的场面。当附近农村的一群人,有组织的跑到公司的煤矿去,明火执仗地砸坏工业设施、抢走企业财产。矿上那么多的干部职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单位被砸被抢,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他脑海里一直悬念着这样一个问题,用一种什么办法,才能把职工和企业的利益真正连在一起呢。
他把今年的工作重点,放在新公司的租赁工作上。他想通过由内部职工出资入股的新公司,租赁经营原企业下属单位的办法,以防这些单位被分而“化”之;同时还能或多或少的起到把职工和企业的利益连在一起的作用。他的另一项工作重点,就是为将来接替他的人创造一切条件,让他经受全面工作锻炼,为以后平稳过度打好基础。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既是为了工作,同时也自然有他的小算盘。自己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得罪的人自然不少。虽然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但也难免不遭人记恨或报复的。这些在台上倒无所谓,可是一旦下了台,那个时候再有人找麻烦,可就只有依靠新的公司领导了。他自然明白,将来的新领导对你如何,就看你在台上的时候如何对他了,所谓人心换人心吗。
拿到县里的批示后,他一鼓作气,依次组织落实了由新公司全部租赁经营原企业下属生产单位的工作。同时,作为新公司董事长的他,随即把新公司的人财物等经营管理大权,一并交给由他提名并由董事会研究聘任的总经理来掌管。而他自己自愿的只留在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的、但棘手的问题却一点也不少的原公司里工作,以便让新公司集中精力抓好租赁单位的经营管理。至此,事实上他已经完成了和将来接替他的人的权力交接工作。
办完以上事情后,他觉得轻松了许多。不过,这突然一下子不管这么多生产单位了,心里不免又有些许的空虚之感。
这时,公司机关里的一高人却发出了由衷的叹息:“唉,这回他可是彻底的钻到套儿里边去了。”
一转眼,春去夏来。这个夏天最炎热的时节开始了。
这天下午,支河恩接到县里的通知,他急忙从外地赶回。当他赶到公司参股的改制电厂招待所大会议室时,这里早就坐满了人。他发现一张张熟悉的但比平时显得有点严肃的面孔,都在用异样的眼神悄悄地瞅他一眼,随后就又迅速地避开了。那表情似乎是怕和他的目光相遇似的。这个宽敞的大会议室,对他支河恩来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曾几何时,在这里,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曾给他颁发过“优秀企业厂长(经理)荣誉证书”。他明白这个证书的背后,是公司上一年度实现利税过千万的结果;而这个数字的背后,则主要是发电厂实现的,那个时候电厂还没有改制。在这里,曾经召开过让他为之蒙羞的电厂改制现场会,那是他一生都无法挽回的遗憾。还是在这里,市主管部门的领导,对他想通过职代会收回电厂改制的行为,曾大加指责,他因此险些被免职。今天还是在这里,他非常清楚这将对他意味着什么。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静的有点出奇。与会的人员有公司班子成员、机关科室负责人和七、八个下属单位的一把手。人们一个个都静静地坐在一个用一张张小桌子拼成的大长方形案台的两侧,好像在等待着有什么重大事情的到来。主席台这一侧,有几把椅子稀稀拉拉地摆在那里,看来上边的领导还没有到。支河恩迅速地扫了一眼会场,然后绕过主席台,径直地走到大型案台的右侧,在公司班子成员就坐的下方,找一空座位坐下。他刚一入座,坐在他上方的一个副经理立刻站起身来:“支经理,你怎么能坐这儿?来,你坐我这儿。”然而,他没有动。
“吱”的一声,会议室的门开了。一个身材矮胖、但天庭非常饱满的人,在公司的人引领下走了进来,他就是主管工业的吴副县长。在他的身后跟着几个随行人员,其中那个仪表堂堂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人事局何局长。
吴副县长刚一屁股坐在主席台的椅子上,便态度和蔼地说道:“让大家久等了。本来早就想到公司来看看,可老是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的,一直也没来成。噢,时间宝贵,不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了。下来咱们书归正传,先由何局长传达县政府党组文件”。这时人们都把目光转向何局长。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来,随后便开始一字一板地宣读起来:“县政府党组文件(2006县政党字第1号)。经县政府党组研究决定:根据工作需要,免去支河恩同志北山能源公司经理、党委书记的职务。此决定自宣布之日起生效。2006年7月10日。”这一刻,支河恩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中暗道:“终于解脱了。”可是,这种感觉马上就被随之而来的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所取代了。会场上依旧是出奇的静,静的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人们只是静静地竖着耳朵,目不转睛地看着何局长。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又拿起第二张纸来,不用说这肯定是接替支河恩职务的以及新班子成员的人事任命了。宣布的新班子名单中,除了继续留任的原班子成员外,只是新增了一名副经理。听到这里,支河恩突然想起了那个对他刺激非常之大的声音······。宣读完毕后,何局长又补充道:“刚才念的是底稿,正式文件待打印出来以后再发给你们”。人们依旧竖着耳朵,好像还没听完似的,会场上仍然是一片沉静。“怎么?你们不欢迎欢迎吗,这以后可还是你们在一块打交道的机会多啊。别看俺们忙活这大半天,等一宣布完就没事了。可你们不一样,下来还得在一块共事儿。”何局长一边不急不慢地说着,一边向刚刚宣布的新班子成员就座的地方瞅了一眼,“你们别看他们坐在这儿一个个跟没事人似的,实际上俩眼光瞅着你们哩,看你们今天表现怎么样,谁欢迎谁不欢迎,是真欢迎还是假欢迎,心里可记着哩。别看他们现在什么也不说,保不准那一天领导一不高兴,找个借口就给你个小鞋儿穿什么的。你们以后共事的时间长着哩,这磨道里找脚印的事儿还不容易吗。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事儿我已经说清楚了,下来该怎么着,你们看着办吧。”经过他这一通调侃式的提醒,人们这才反应过来,接着便响起一阵掌声。这时再看何局长,他依旧悠然地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仍然没有一丝表情。不过,明眼人一眼就从他这一通溢于言表的调侃中,看出他内心里抑制不住的喜悦之情。
会场上又恢复了原有的沉静。“下面欢迎吴县长讲话”。随着一名随从那带点硬邦邦的话音儿落定,又一阵掌声响起,再次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静。 “支经理曾不止一次地找过县长,主动要求辞职,把位置让给年轻人。他态度非常诚恳,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受党教育多年、长期在领导岗位上久经考验的老经理的高风亮节。县领导根据他的多次要求,最终才同意他辞职。关于这一点,在来这儿之前,县长还特意嘱咐,一定要当面向大家讲清楚”。听到吴副县长讲到这里,支河恩心里在想,对他来说有这几句话也就足够了。起码说明是他先提出来不干的,而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免的他就行了。接下来吴副县长话锋一转:“新任经理年轻有为,有能力,有魄力,德才兼备,深受大家的拥护。在组织考察的时候,大家都一致推荐他,都对他投赞成票,这种情况在别处还真不多见。可以说他当这个经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吴副县长这番无论对下台者还是上台者都适合的话讲完以后,便把目光转向支河恩,他笑容可掬地说:“支经理说两句吧”。支河恩的“下台演说,”自然不在话下。不过,面对这样的场面,他想到再也不能和眼前这些一直理解和支持过他的管理人员一道工作的时候,却不由得萌生出一种感慨之情。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流露出来,以免显得小气或被人误解。可是,当他发自肺腑地说到:“这么多年来、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不可能干到今天。”的时候,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微微地向在座的公司人员欠了欠身,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轮到新任经理、党委书记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支河恩这时才注意到,眼前这个他看着一步步从基层走到公司领导岗位、现在又刚刚接替他的年轻人。他发现他是那样的沉稳,一切都显得胸有成竹的样子。那轻松的神态,似乎这一切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又似乎他掌管公司的全面工作,只是件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支河恩不由得联想到十三年前,他在就职演说时所流露出的拘谨和内心里忐忑不安的心情。
新经理的就职演讲,紧扣人们关心的企业发展主题,他讲的发展目标,非常振奋人心。支河恩随着他描绘的蓝图,仿佛看到达到目标后的公司所呈现出的一派新面貌和新气象。他不得不佩服他的魄力,深感自愧不如。他心里隐隐地在想:看来自己辞职是明智的。应该再早一点就更好了,如果新经理早一点被任命,对公司的发展可能会好的多。那个时候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比现在要好一点······。新经理最后以非常自信但又显得很轻松的口吻说:“这些发展目标,不是什么难办的事,用不了费怎么大的劲儿就能达到。大家只管放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企业发展、项目和资金这方面的事,我来办。我相信,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只要公司上下团结一致,我们的目的就一定会达到,北山能源公司的明天会更好!”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掌声。即使心里不是滋味的支河恩,也由衷地为之鼓掌称赞。
短暂的会议很快结束了。支河恩一向看重并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这个职务,也在这一瞬间随之结束了。不过,他那种说不上来的不是滋味的感觉,却依旧丝毫不减的埋在了心中。面对散会的人群,面对这些打过多年交道的、以后可能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的工友们,此刻的他无论心情如何,却依然和他们谈笑着话别,并一一目送他们离去。当视线中再也看不到他们远去的身影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莫名的凄凉之感,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支河恩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当路过电厂那栋办公楼时,看到还有稀稀拉拉的窗户里透着灯光。他边走边侧视着眼前这栋既熟悉又生分的办公楼,心中若有所思。在他缓缓地转过头来的刹那间,突然,头顶上响起了一个清晰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你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仿佛看到在他头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刻板的面孔,正在俯视着他。那眼神中透露出的,说不上是怨恨、还是嘲讽或是怜悯。当他壮着胆子,再定睛细看时,那个影子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眼前只有依稀可见的几盏昏暗的路灯,照着他长长的身影在水泥路上晃动。不过,现在他心里似乎明白了,一年前他曾经的一个同事,最后留给他的这句话的含义了。难道一年前,他就知道我有今天这一步吗?那······。支河恩想起了许多往事,但此时此地的他,最想要的是早一点回到家中,他一刻也不愿意在外停留,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家的渴望。
他刚一脚跨入家门,便感到这颗一直不是滋味的但在外边又不得不强撑着的心,才缓缓地落下。早在家里等候多时的老伴,这时也闻声迎了上来。她今天是特意从打工的县城里赶回来的。
“怎么样,宣布了?”她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脸。
“宣布了,这回是真的了。”他淡淡地笑了笑。
“你从市里调回来,后悔吗?”
“这倒不后悔。”他不加思索地如实回答。他不大习惯政府部门里那种平平淡淡的工作,那年他三十六七岁,功名心很强,一心想回企业体验一番自我价值,轰轰烈烈地干点事。就是现在被免职了,他也确实不觉得后悔。好歹说起来在这个几千号人的大摊子里干过一任。
“当时光人到这儿来,不把市里的编制、工资关系什么的开过来就好了。现在倒好,弄的连个退路也没有了。”她无不埋怨地说。
他沉默不语。心想,那个时候只想着怎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摊子里先站住脚,谁会想到现在呢。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满脑子里好像一团乱麻,这一时半会儿还理不出个头绪来。以后的事,等脑子清静一点再说吧。”
“还能在公司里干点别的工作吗?”他犹豫了一下。 “那是不可能的事。干过一把手的人,免职后不可能还在原单位干。要不谁都觉得尴尬,也不好处。”
“那——”她还想说什么。但当她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又把话咽了回去。夜深人静了。支河恩呆呆地坐在小客厅里,不知如何是好。以往这个时候,正是他静下心来,梳理一天的事情,考虑明天需要做的工作的时候。而今夜就用不着了,以后也用不着了。这突然的无所事事,倒叫他不习惯了。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空前的失落感。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从今天起我已经从这里的政治舞台上退出了。刹那间,他脑海里情不自禁的闪现出这十几年来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事件和一张张形态各异的面孔。最后,他的思绪停留在最近为什么辞职的问题上。办完新公司租赁工作并下放经营管理权之后,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实权可言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反常现象出现了。内部的和外界的一些信任他的知情人士,将他们看到的或听到的一些明显有悖常理的现象告诉给他,提醒他引起注意;同时,无意中他也察觉到了,这些反常现象竟然是冲着他的职位来的!他愕然、诧异、不解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十几年来,他的职位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晃动。不过,那都事出有因。或是他得罪了一些难斗又难缠的主儿,招致无休止的上告于他;或是他没有满足某些人的私人要求,他们则利用或挑动周边农村的人,对公司制造摩擦和干扰活动,给他难堪,并借此造成上级对他产生处理不好地方关系的看法;或是他对某些问题上的做法,让领导难于接受等等。可是,这次却是为什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感到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和羞辱了。此刻,他想起了多年来一些和他交心的人,对他在个别用人问题上的一次次提醒;而他却固执己见,还以敢提拔不怕超过自己的人而引以自豪呢。现在果然应验了上级那位非常信任他的人的预言,他脑际间再次浮现出那个充满着忧虑的眼神。他百感交集,在痛恨自己昏聩的同时,心里一滴滴的在滴血。然而,却又欲说不能,欲哭无泪。面对那个正在步步向他的职位逼来的灵魂,他必须尽快地做出应有的对策。
他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巩固自己应有的地位。虽然他知道自己在位的年限不长了,但是,就是在位一天,也决不允许像这样任人宰割。他还想,我自己下台可以,但绝不允许被人挤下台。不然,丢不起这个人。靠什么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呢?他厌恶那种对上不惜慷公家之慨,巴结权贵,保官要官;对下诱以名利,拉拢利用那一套。他试想着要是在内部搞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目的的活动,这样做会得到人们的支持吗?猛然,他犹如大梦初醒:你现在还有这个资本和条件吗?此刻,他的耳边再次回荡起一个信任他的人的声音: “你现在把新公司的大权都下放了,手里没有什么拿头儿了,这以后要是万一有个事儿,可就不好说了。现在的人们都讲实惠,谁管着他,谁能给他好处,也不管这事儿应该不应该、对也不对,他就会说谁的是,就会跟着谁跑;这么说吧,你别看现在表面上人们对你还差不多,可要是真正到了事儿上,恐怕有一半的人不会站在你这一边,而会跟着管他的人走,因为现在你已经管不着他们了。”他再次痛哭地品尝到放弃领导权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滋味。他还想到,以前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甚至对自己的失误也能够给予理解,那是因为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公司。而现在要搞巩固自己地位的出发点则纯属为了个人的权力,性质完全不一样了。因此,这样做恐怕难于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一旦盲目地做起来,到那时弄得上不来下不去,岂不贻笑大方?而且,自己多年来在公司的形象,弄不好也会随之毁于一旦。可是,要是不这样做,就意味着眼睁睁地看着,他应知的信息被封锁、应有的地位被一步步架空、名存实亡——。如此做也难、不做也难,究竟该怎么办呢?此时的他犹如陷入深深的泥潭之中,正在苦苦地挣扎着。恍然间,他仿佛看到就在不远处的岸边,依次出现了一个个非常熟悉的脸庞和身影。他竭力掩饰着内心的羞涩和恐慌,显得很平静的样子目视着他们,但心里急切地渴望着他们的救援。可是他们的表情都是那样的冷漠,一个个眼看着他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却没有一个人伸手拉他一把。他呆呆地看着这一张张既熟悉又冷漠的面孔,一一从他的眼前消失后,不禁仰天长叹一声,顿感一切都无可依赖了。眼下的处境,只有靠自己想办法脱身了。可是,举目这茫茫的泥潭,出去的路在那里呢?他焦躁的搜寻着出去的路径。顿然,眼前又梦幻般地闪现出一张张他任职以来免职人员的面孔。那一双双无不透露着怨恨和讥讽的眼神,似乎在说:原来你也这么怕丢乌纱帽哇,那你免别人的时候,想到过他们的感受吗。怎么,现在轮到个人头上了,就现原形了吧。看来你比别人这不也强不到哪儿去啊。那一双双讥讽的眼神,最后不屑一顾地瞥了一眼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的他,便一一心安理得地离去了。绝望中,他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发呆。忽地,他眼前一亮,走在最后边的那个人站住了,只见他缓缓地转过身并向他这边走来。他顿感还有一线希望尚在,便急切地向那个人投去求救的目光。近了,他看清楚了那个人清晰的脸庞,他们之间还都比较了解呢。不过,他马上又从他那冷漠的面孔上看出,他并没有拉他一把的意思。他只是毫无表情地看着深陷泥潭里的他,淡淡地留下了一句似乎是提醒抑或开导的话:大不了不干了不就得了嘛,何必这般模样,让人笑话。你见我们不干的时候,有谁求过你一句话。说罢,只见他默默地摇了摇头,便转过那张冷若冰霜的脸去,也从他的眼前消失了。他从如梦如幻中回到现实中来,还依然觉得仍有一张张冷漠的面孔和一双双鄙视的眼神在面对面的看着他。这一刻,他冷静下来了,虽然非常看重这个职位,但更看重名声的他,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巩固自己地位的事不能做。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另一种选择,暂时可保自己的职位:忍气吞声,甘当傀儡。可是,那岂不比下台还难受!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下台。既然下台,何必不下的体面一点呢。于是,他从心底里冷静地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主动辞职。他不得不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职位是断送在他自己手里的,是自食其果,又能愿得了谁呢;同时,他也自认为也应该用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昏聩抑或工作中的失误以及因工作对不住的人做一个了断。
恰逢他做出这个决定但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的时候,一个对他刺激非常之大的声音,不早不晚地出现在他的耳边:“公司历届一把手,数你干的时间最长了;别人干得最长的也不过十年八年,你这一干就是十三、四年了。其实,谁跟谁那两下子都差不了多少,时间一长,浑身的解数就使完了,再也就拿不出什么新鲜的招儿了,永久不是那一套,人们也就没了新鲜感了。以后不管你再怎么说,人们也早就麻木了。这样就是再干下去,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不如该收就收吧,现在是时候了。”他非常明白,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你在这里执政的气数已经到头了。面对这番直白的“劝退,”他心里感到一阵阵酸痛,胸膛内在翻江倒海,他那根敏感的神经被深深的刺痛了:难道我真的落下了老马恋栈的骂名吗?难道人们对我的看法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吗?他强忍着满腹的酸楚,把从胃腔里翻上来的一股逆流一口气咽下去,然后什么也没说,他觉得这个时候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就要下台了。他静静地坐在伴随他度过十几年艰难岁月的即将告别的办公室里,默默地在想,下台,对他早就不是什么难接受的事了,何况总有下台的这一天,何况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何况即使干着也无异于受罪呢。下台,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只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下台,叫他心里不是个滋味。
不几日,他趁在县政府办事的机会,悄悄的叩响了县长办公室的门——。
在等待上级宣布的日子里,时逢新公司没有租赁的公司医院正在和县医院进行联合办院股份制改造。为了医院改革、扩建以及统筹安排方方面面的工作的需要,急需由双方组成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医院的工作。这样一来,原有班子成员需要解除职务,而且刻不容缓。他不想在最后落下不作为的话柄,因此,在宣布他免职前,他最后又做了一次“恶人。”
夜,越来越深了。支河恩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小客厅里早已烟雾缭绕。他仿佛看到那烟雾飘渺的背后,有一张张不同形态的面孔正在面对着他。有疑惑、无奈和忧虑的,有讥讽、狞笑和得意的。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后半夜,外边静悄悄的。他移步到阳台,漫无目标地仰望着浩瀚的星空走神。他彻夜未眠,直至群星隐退,天空泛白。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意味着昨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他依然沉浸在往事之中,而对于未来,他却一片茫然。
支河恩被免职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外界首先给他打来电话的,没想到是易老板。这易老板在塞外买了一座煤矿,支河恩在位时,在易老板的一再邀请下,他曾派公司的人去管理这个矿,并顺便安置一些下岗职工。从此二人相识。易老板在电话中关切地问道:“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以后的打算——”支河恩略微停顿了一下。 “以后的打算,我还没想好,反正怎么也得找点事干,到时候再说吧。”
“要不你到我那个矿上去吧。咱自己有矿,还到别处去干嘛。再说,矿上管事的,是你们公司的人,又是你的老部下,你们在一块打伙计,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支河恩在明白易老板的意图的同时,脑海里早就闪现出那个整天介刮着黄毛风的地方,而且风中还夹杂着煤面儿,到处都是黑不溜秋的。他仿佛看到,在那个荒凉的连洗澡水都没有的煤矿里,他整天蓬头垢面,除了下井就是钻在简陋的宿舍里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他还想到,夹在易老板和公司之间,在那里做事会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场面。想到这里,他脸上好像在一阵阵发烧,那颗敏感而有极爱“面子”的自尊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深深地刺了一下。心想,我就是再不济,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份上吧。他毫不犹豫的谢绝了易老板的邀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虽然现在不当经理了,但是,找一份起码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差不多的差事,还是不成问题的。
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开始了闲居的生活。
刚开始,他在家里还憋的住。何况他也想好好的清静清静了。再说,过去的同事或工友,还时而约他一块聚聚,因此,他倒不觉得孤独。可是,时间一长,别人谁都有谁的事儿做,也就顾不上他这个大闲人了。他整天憋在家里,无事可做,越来越感到这样的生活太枯燥乏味了。他又不愿意到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去,怕给人们添麻烦。再说人家见了他,陪也不是,不陪也不是,这样自己也会觉得难堪。因此,就不如干脆不去,人要有自知之明。他也不愿意到户外去,下台以后,他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怕见人的感觉,好像别人会笑话他似的。他只好窝在家里,尽管家里枯燥乏味,可也总比在外边让人看见好受的多。
他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了。如今的他犹如被困在囚笼里一样,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苦恼,他仿佛与这个世界隔绝了。他把他的这种感受,打电话告诉给了一个敢说点直话的工友,试图缓解一下憋在心中的郁闷。没想到这个工友的一番话,更叫他雪上加霜了:“你现在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事。你看看人家过去当头儿的是怎么做的,而你又是怎么做的,你略微一想就明白了。人家是把干部们的家属和子女转工转非,而你哪年调资却把指标全都给了工人,干部们谁都没调;人家是把凡有点关系的那怕是多少沾点边的人,都一个个调到机关去,而你却把机关里那么多的人精简下岗。人家就是不干了,这些给他们办过事和沾过光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人家。到了事上,不用说他们就会主动赶去帮忙;就是没事儿时,也会经常不断地去看望人家,所以人家什么时候也不会门庭冷落。而你就不一样了。人们对当过领导的人的看法,往往是拿他和前任比;有人家前任在这儿比着,不用说你也会明白,现在人们会怎么待你,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当然明白这一番话的言外之意,可此时的他,又能说什么呢。从此以后,他知趣地不再主动跟人联系了。
他越来越不愿意过这种蜗居的日子了。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外出打工。
他向在省里工作的同学、朋友,发出了帮他在外地找份差事的求助信息。他期盼着时间不长就会有接收单位的消息传来。
有了想法,有了盼头,他一直灰暗的心里似乎透出一丝光亮。现在他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家门,到户外去转转了。遇见熟人搭起话来,他完全可以说,时间不长自己就可以到外地做事去了,也就不觉得总是窝在家里那样尴尬了。
他日思夜想,无时不在憧憬着,从这里走出去,走到那个尽管他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但那里有他得心应手的工作可做,因而可以有意义的生活了。他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不久,他得到回音。说现在好一点的单位,都不缺人手;需要等以后有机会再说,要他耐心等待。
半个月过去了,没有结果。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
时光日复一日地白白流失着,渐渐地他对在外谋职的事,越来越感到渺茫了。不过,他还存有些许的侥幸心理,心想,总不至于连份打工的差事也找不上吧。他只好耐着性子继续等了。
他又不愿意出门去了。怕见到熟人,人家会用嘲笑的眼神看着他:这么一个大活人,成天介闲在家里,到头来连点活儿也找不上;就这点本事,以前怎么当经理来哩。他只好又过起了蜗居的生活。然而,即便这样,随着时光的流逝,他还是觉得,在他的脑后总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在冲着他嘲讽:看,他也有今天。
看来他以前当经理,并不是有什么本事,要不怎么一下台,就连个活儿也找不上了呢?真正凭本事吃饭就不行了。这号人除了窝在家里,还能干什么呢。
哼,也该让他尝尝下岗是什么滋味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他得到的回音,仍然还是那两句话。事到如今,他不得不反思:这是不是人家都不愿意要一个下了台的人呢,他为什么下的台呢?他已经预感到,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下去了;要想尽快走出去,必须另想办法。可是,别的办法又在那儿呢。他开始后悔在位时,为什么不先把后路铺好,以至现在想出去找份差事都这样为难。
老伴怕他常这样下去会憋出病来,又从县城赶回来,劝他先在附近找点活干着,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不迟。
“这附近能有什么活儿?”他带着几分疑惑问。她犹豫了一下。“活儿倒是有的是,就看你敢不敢去了。”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活儿,有什么敢去不敢去的。”
“翻大车!你敢去吗?”他惊讶地看着她,好像不认识她似的。同时,他脑海里早就浮现出这附近马路边,那一个个煤尘飞扬的小煤场。煤场内,时而停放着两、三辆大卡车。一群中年男女,每人手持一把大铁锹,他们时而在车上把从外地拉来的好煤一锹一锹地卸下来,时而又在地上把堆放的次煤与卸下来的好煤一锹一锹地掺和均匀,最后把掺和均匀的“混煤”再一锹一锹地装上车。直到货主验收通过,拿到应得的那一份钞票,这一辆车的“翻车”工作才标志着结束。接下来再转到下一辆车上去,继续重复着以上工作。这一系列的劳作过程,就称之为“翻大车。”他仿佛看见,自己混在这支“翻大车”的队伍中,头发和衣服上都落满了煤尘,特别显眼的是,鼻孔处沾着一层厚厚的煤面儿,几乎不显面孔。他不敢想象,以前的同事和熟人看到他这幅模样,会是一种怎样的尴尬场面。想到这些,他冲着在一旁等他表态的老伴,狠狠地甩出一句:“我就是到外地去要饭,也绝不在家门口干这个。”
“我就知道你抹不下这个脸来。”她接着说:“家门口有活儿,你怕丢人现眼;人家易老板要你,你又怕这怕那;你想让同学帮着找个好一点地方,要是有这样的地方当然好,可这都等了两个多月了,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这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要不你先到易老板哪儿去吧,好赖在哪儿有个活儿先干着,不管怎么说,也总比在家里这么憋着强。我一个女的都这把年纪了,还出去打工;你一个大男人干嘛这么怕这怕那的,在那儿都是凭干活吃饭,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他这才明白她开始说的“翻大车”的用意了。
一阵沉默过后,他油然地想起了以前搞的那次机关大精简。当时有那么多人下岗,他们那个时候的处境,和自己现在不是一样吗。说不定他们当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遇到的困难比自己还要大呢。此刻,他仿佛看到他门在煤尘飞扬的煤场里,正在手持大锹,一脸尴尬地“翻大车”的身影。他们不都是一些爱面子的人吗。
两个多月来,他在心理上经受了难以名状的磨难。不知不觉中他渐渐地回到了一个原本的平常人的心态上来。这时,他想起了那位饱经沧桑的老领导说过的那番话:“你在台上的时候,这时的你并不是真实的你,而是你扮演的那个角色;等你下了台,卸了妆,去掉一切伪装的东西以后,这时的你,才是真实的你。”他现在似乎觉得,找到真实的自己了: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职工,一个为了从下台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而急于走出去的准打工者。
急于想走出去的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无奈地想起了唯一邀请过他但又被他谢绝的易老板。他在感情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可是,每当他走到电话机前,心里就不由得“砰砰”乱跳,几次想拿电话的手,不由自主地都缩了回来。他踌躇半响,最后还是忍受着自食其言的尴尬,羞涩地拨通了易老板的手机。
一辆银灰色轿车,停在电厂家属院大门口。他匆匆拎上行囊,终于走出了这个连续蜗居了两个多月的家门。在准备上车的那一刻,他不由得回过头来,深情地望了一眼这个马上就要告别的家。心想,多亏了它!在他最孤独、心情最糟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安身的地方。这时,他忽然又想起了为了他的生活免遭干扰、主动给他提供这套住房的那个同事。蓦地,他头顶上仿佛又响起了那个清晰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你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再次由衷的萌生出几分悲凉的感触。
车子很快开动了。透过车窗当看到公司的一座座建筑物,一一从眼前闪过时,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似的。不大一会儿,车子便驶出了公司的地界,疾驶在北上的山区公路上。明明知道公司已经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连绵的群山已经隔断了视线;可他还是忍不住的回过头来,透过后车窗向后凝望良久。别了,北山能源公司!别了,这个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地方!
时至仲秋。公路边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透着一股自然的纯净的美。他觉得这一片天空,是那样的湛蓝和安逸,连空气都觉得清净和新鲜。他像是刚从笼子里逃出来的一只鸟儿,终于可以自由的飞翔了。下台以来,他一直憋闷的心情,第一次感到豁然开朗了。不过,这种心情很快就被面临的新问题所取代了:到了易老板的煤矿,夹在私企老板和公司之间,毕竟处境尴尬。就这样,他怀着刚刚走出来的喜悦和又面临着尴尬的复杂心情,第一次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一条明知存在着尴尬但时下又不得不走的路。然而,不管怎样,他毕竟走出来了,从下台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后记
第二年,支河恩谢绝了易老板的挽留,离开了那个毕竟感到尴尬的工作环境。随后,在省局领导的引荐下,来到了人地两生疏的太行山腹地,在一座铁矿山打工。从此,他真正走上了一条艰难而又有意义的打工之路。在漫漫的打工生涯中,他曾不断地遇到来自自然方面的和外界人为方面的种种危险。可是,每当他感到实在难于干下去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段不堪回首的蜗居的日子,从而无声地激励着他又继续干下去了。
若干年后,因种种原因,北山能源公司已经名存实亡。消息传来,他脑海里愈发不断地浮现出那个光秃秃的山丘环绕着的北山能源公司的轮廓,还有那些曾经理解和支持他的人们的身影。
告别公司多年以来,偶尔遇到公司的或是周边农村的凡了解他的人,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别的没落下,就落了一个人。”开始他对这话并不以为然,只不过见了面总得找两句话说说而已。可是,后来说的多了,即使匆匆相遇,寥寥数语,还是仍然离不开这句话。他这才渐渐地意识到,原来这是了解他的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看法。他感到些许的释怀。
同时愈发感到,当初做出的那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是理智的,不然,人们对他还会 是这样的看法吗。2018年1月31日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4 小路(三十 )
- 浏览:53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2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7 樱花树下
- 浏览:47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0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297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9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41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8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90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4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50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5 换妻
- 浏览:16248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3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