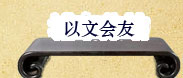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浭水流》第一部第二十一章 
纪实体家史小说《浭水流》第一部血洒冀东
第二十一章 村庄寂静
诺大的一套宅院,关押了几十人,竟然鸦雀无声,只有达民和警卫的脚步打破了古墓般的静寂。静默是有重量的,重到能将人压垮,死寂比喧嚣更让人紧张。此时的张达民仍抱有幻想,希望这一切都是误会,只要跟县长细谈,肯定能洗清罪名。
“最近你都干啥了?”县长坐炕上,翻看炕桌上堆满的坦白材料和检举信。
被绑着的达民站地上答,“前几天,带突击队端了开平警察所,缴获十几条枪,今儿又和张志发打死两个特务、缴获两只盒子枪。”
于沐之听完露出赞许的神色,口气和缓地说,“老罗的案子没你的事,考虑到你脾气暴躁手黑,所以限制你的自由,等案子了结再安排你工作,你先在这儿呆着。”
听县长这么说,达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本想问问叔叔到底犯了啥罪,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回到羁押室,铁成关切地询问。达民就简单地给他讲了一遍过程,铁成说,“你这态度对,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犯倔。你叔叔要是像你这样不就没事了?”
“我叔叔是不是也在这儿?还有别的屋子关人吗?”达民急于知道叔父下落。一听这话,铁成像被烫了似的急忙缩回去,躲到一边。
看押他们的警卫换班,达民惊喜地看见本村的李宝贵,县委公安大队的战士。在这种情景下相遇,达民踌躇该不该打招呼。
“咦,这不是张达民吗?你也进来了?”小李胆子挺大,也挺重情义,主动跟达民搭话。听说达民还饿着肚子,就给他拿来一包点心和一壶茶,“没饭了,先垫补垫补吧。”
一点胃口都没有,呷了口茶,满嘴苦涩,从后院传来拷打和审问的声音,掺杂着喊冤和痛苦的嚎叫,达民听声音像叔父,“老罗也在这儿吗?”低声问小李。小李脸色一变,连连摆手,迅即退到门外。
一提老罗,都谈虎色变,可见这案子非同一般,达民因县长的话而轻松的心又沉重起来,处事轻率的叔叔恐怕凶多吉少。绑着双臂歪在炕梢,胡思乱想的度过不眠之夜,一大早,又被叫去见县长。
“还捆着?”于沐之有点惊讶。
“捆得手都麻了。”达民说。
“来,给他把绳子解开。”
警卫应声进来,解下绳子。达民赶紧活动麻木的手臂。
“绑棉袄里面吧。”县长想了想又说。
绑在棉袄里,外表看不出来,给被绑者留住体面,算是提高待遇、降低惩处力度,说明问题他的问题不严重。这次绑得位置也比较高,双手能做小幅度活动,吃喝拉撒都无须他人帮忙,达民感觉舒适很多,心理负担也为之减轻。这次县长没问什么,只是吩咐不再跟那些人关一起,在中院找个空屋子单独关押。
“县长说了,你就在这儿看书学习。”警卫把达民关进中院的西厢房,锁上门走了。
看书?哪儿有书?学习?学什么?手臂绑着,腿脚自由,达民就在屋子里转悠。这是间宽敞的西厢房,雕花窗户底部格子镶着玻璃,能把庭院看得清清楚楚。屋子里的家具都是红木的,炕上的被褥也是绸缎面洋布里子。不错,这辈子还没睡过这么好的屋子。达民把被褥铺到炕上,带着苦中作乐的心情躺上去,合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被痛苦的嚎叫惊醒时,已经是中午,太阳把院子照得明亮,却不见一个人影儿。嚎叫声消失,也不知是拷打结束,还是被审讯者断了气,庭院恢复平静。达民感觉太静了,静的让人喘不过气,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寂静让人更觉饥肠辘辘,胃翻腾,脑子里也翻腾,管他是剐是杀、是死是活,先吃饱再说。达民就喊:“老大娘,老大娘,我饿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他犯经验主义,以为县委住地肯定雇了中老年妇女做饭,所以这么喊。结果是喊了半天,来个年轻姑娘,长得挺壮实,穿了件破旧的花棉袄,一根枯黄的长辫子蓬乱地垂在脑后,右耳到下颌处一道明显的伤疤,看着超不过二十岁,神情却像遭遇过百年炼狱。
“喊啥?我们这儿没有老大娘,就我一个人。”姑娘脸色阴沉,恶声恶气。
咋就你一个人?达民差点脱口而出,突然记起这是潘家峪,一千多村民被日寇屠杀,只有几个青壮年幸存,因此没有老幼。“老大娘”这个称呼触到姑娘痛处,让她想起了被屠杀的亲人。达民立刻明白了为何年轻姑娘如此神情,惨绝人寰的遭遇夺去她所有的欢愉,留下载满仇恨的空壳。
“对不起,别生气。是我一时疏忽忘了。”达民恳切的道歉。
“你喊半天,到底啥事?”
“从昨天到这儿,我还没吃饭,实在是太饿了。”
“那你为啥不出去吃?”姑娘脸色缓和。
“我是来接受审查,不让出去。”
姑娘看到了他棉袄里的绑绳,“受审查的都关在那边西屋,你咋…..”话到嘴边急刹车,默默转身去做饭。
姑娘端来一碗萝卜汤两个玉米饼子,达民狼吞虎咽地吃完,又开始想办法消磨时间,必须干点事分散注意力,免得老想眼下的处境。在抽屉里翻出个小本子和铅笔,试了试,手能写字,他就在小本子上练字。
“大姐,你还把门从外面扣上,别让人怀疑我想逃跑。” 姑娘来收拾碗筷,达民叮嘱道。
“关了这么多,没一个跑的。”话虽这么说,还是咣当一声从外面把门扣上。
逃,就是背叛。不跑,一半是出于忠诚,一半是无处可逃,从抗日队伍叛逃,除了投敌,还能去哪儿?逃与不逃,都是死路。
西厢房的门和窗都是朝东,午后就照不到太阳,早早陷入黑暗,没到傍晚,就看不清纸上的字迹,手臂也有点发酸,达民就呆呆地坐着,寂静中的听觉特别敏锐,后院传出的轻微呻吟都能听清,他在那一声声嚎叫和呻吟中极力分辨是否有叔叔的声音。如果能嚎叫,起码还活着。白天只是拷打,处决都是夜里进行,不用刀不用枪,村外庄稼地,挖个坑,活埋。拷打中死亡的,也是夜里拖出去埋掉。达民的耳朵越来越灵敏,他甚至能听出被拖拽的是死是活,尽管活的也堵住嘴发不出声。
惨白的月光下,这个被日寇屠杀焚毁的村庄,阴森死寂,夜风吹过,叶声沙沙,荒草蓬蒿中,鬼影幢幢、冤魂荡荡。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个白昼都有人被带来,每个夜晚都有人被拖出。没有提审,没有谈话,一天天,张达民就关在西厢房里练字。领导是把我忘了吗?还是定不下来杀和放?每个傍晚都可能是最后一夜,每次的脚步声都可能是行刑队。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等待死亡,惴惴不安的等待是慢刀子杀人。四五天后,一个雾锁云埋的傍晚,天黑前起了风,庭院里树木摇晃,枝杈斑驳的影子投到地上,像鬼魅的手指彼此搔抓。
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达民听出,不是送饭的姑娘,起码有三四个人。
“天还没黑,今儿提前,这么早就动手吗?”
哗啦一声,房门大开,进来一位身着呢子大衣脚踩革履的中年男子,在几个警卫的簇拥下更显威风凛凛。尽管室内光线昏暗,达民还是一眼认出来人是中共唐山地委焦专员。
焦专员未料到屋子中有人,楞了一下,不满地问道:“你谁啊?怎么在这儿,这是我的屋子。”
“是别人让我在这儿呆着。”达民也同样诧异。
“出去!”专员粗暴地命令道。
“去哪儿?”张达民不知所措。
“爱去哪儿去哪儿。”焦专员没好气的说。
焦专员亲临丰润主办“汪派国民党”一案,一言九鼎,手握生杀大权,是杀是放,一锤定音。惹专员生气,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识时务的张达民赶紧滚出房门。
到了院子,却无处可去,漫无目的的徘徊。去找领导,也许是找死,领导想不起来,还能多活几天。不找,怎么过夜?考虑再三,决定求见县长。
于县长正在几张纸上签字,见达民进来,用衣袖擦了擦眼睛,带着很重的鼻音对警卫说,“给他把绳子解开,上通讯班呆着吧。”
县长分明是落泪了,是因为签署那些处决令吗?达民暗想。到了通讯班,竖起耳朵听别人聊天,捕捉有用的信息。通讯员聊的都是抓了某某,活埋了谁谁,谁挺能扛,谁一打就招。不时听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终于有人说到罗春一。
“老罗是在北岭被捕,然后转到潘家峪,到这里时脑袋已经打得有半个斗那么大了,但是还能要烟抽,又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
说这话的人忽然意识到什么,瞥了他一眼来了个急刹车。达民面无表情,心里却翻江倒海,焦专员的到来,意味着案情重大,受牵连的人会更多,也许叔侄很快就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果然,当天晚上又被叫去见县长,进了门看到书记也在,心里咯噔一下:事情不妙。县委班子中,罗春一素来与杨书记不睦,书记早就对他提拔安插洪麟阁旧部不满,此次肃反,将他们一网打尽,都被打成“汪派国民党”,罗春一则被扣上“丰润总部主任”的大帽子,是主犯,丰润地区最大的汉奸。
今晚的提审,稍有不慎,就是覆水难收,说错一句,出口即死。达民感觉耳朵里有只蝉在尖叫,刺得鼓膜胀痛。
于县长一指杨书记:“认识不?”
张达民立刻恭恭敬敬的回答:“认识,是杨书记。”
侄子的态度与那个倨傲的叔叔大相径庭,杨书记有些意外,绷得铁板似的脸松软了些:“你叔父是汪派国民党的头目,是大汉奸,已经被处决,我们还挖出很多他的同党,你对这事什么态度?”
“杨书记,我是共产党员,罗春一有罪党怎么处置都是正确的,他是他,我是我。”达民立刻说。
杨书记点头: “你这态度对。那好吧,你就先休息,等过几天安排你工作。”正在这时,张一民被绑了进来,达民就放慢脚步,观察事态。
“你父亲是汪派国民党头目,……”
没等书记把话说完,张一民就勃然大怒,跳着脚为父亲喊冤。
“我父亲不是汉奸!你们冤枉好人。”
杨书记马上黑了脸,立刻变了口气,“你也有事,有人检举了你!”
哥俩关到同一个房间,达民悄悄告诉堂兄,“老罗没了。”
“那今后我就当家了,咱们卖二亩地,买点药把我的寒腿好好治治。”这二彪子不该显露亲情时,像个孝子,这会儿没外人了,他又一副忤逆的样子。既然不把父亲的冤死当回事,刚才何必那样?达民真想痛殴他一顿。
“你兜里有钱吗?我还没吃饭。”
达民说还有十块钱。
“那好,让看守给我买几个烧饼。”
看守接过钱刚走,又有几个警卫进来:“张一民,去蹲禁闭。”
“我寒腿犯了,蹲不了禁闭。”不知死到临头,他还满不在乎的耍混。几个警卫不由分说扑上来,连拉带拽的拖出去。
出了门,就传来击打声,一声叫骂后就是嘴被堵住的呜咽声、重物倒地声、擦着地的拖拽声。声音渐渐远去,黑暗如怪兽的巨口,将一切吞噬。
宅院重归宁静,月光皎洁,人间清明。烧饼买来了,却没了想吃烧饼的人。
又是早晨,太阳照样升起,张达民在噩梦中醒来,迎接不可测的一天。房门吱嘎一声打开,李宝贵端着大茶缸进来,用手指蘸茶水在炕席上写了三个字 :“一民无。”然后就转身离去。
已经预想到这样的结果,还是胸口一阵刺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罪无罪,是死是活,全凭掌权者的好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留此地等于待宰。
如何摆脱险境?张达民想到了示弱,没有比病人更弱的了。于是他在炕上躺了两天后求见县长:“我这几天痔疮犯了,一个劲便血,拉得头晕眼花。”
房间没别人,于沐之正在整理炕上的一堆短枪,他明白张达民的用意,就说:“你棉袄里还绑着绳子吧?”
达民说是的。县长就命令给他解开,然后从那堆枪里拿了颗撸子枪递给他,“你带着防身,回家休养吧,等养好身体再给你分配工作,鬼子要大扫荡了,注意安全。”
那堆枪,至少上百支,枪的主人无疑都是因所谓的“汪派国民党”一案被捕的同志,他们当中大部分都已被埋在了潘家峪村子四周的田野里。
私自放走张达民,于沐之是冒了很大风险,因为在处决了张一民后,杨书记和姓苏的组织部长力主铲草除根,将张达民也活埋,以免他日后为叔父和堂兄复仇。
罗春一的案子牵扯人员太多,宅院关不下,就把罪行较轻的关进山洞。直到5月份日寇大扫荡,县委北撤,仍有一百多人被关在洞里,看管他们的警卫都随县委撤退转移,没人给送饭送水,这些人饥渴难耐,最后一齐冲出来,有人主张回家,有头脑清醒的说,“万万不可,如果回家我们就等于自绝于党了。”于是大家一齐去找党组织,大扫荡开始不久,于牧之就牺牲,继任者没几天也牺牲,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第三任,跟县长说,怎么处理我们都行,就是别把我们饿死啊。县长说你们出来没去投敌,就证明罪名不实,回去吧。
关于这一百多人的下落,流传很多说法,这是最好的一种,也有说被活活饿死,也有说被日军放毒气熏死。笔者希望第一种是真的,其他都是无根据的造谣。
罗春一被捕那天,他的通讯员刘兰亭因关节炎正在自己家里养病,被县委派的人找到,交出枪,并未被捕。他感觉呆在原地有危险,就去邻县找打游击的兄弟,途中被日军抓到,押往县城的途中遇大雨,鬼子就用刺刀把他挑了。十二团第一美男子,容貌清秀得像女孩的刘兰亭,开膛破肚地倒在路边,横尸暴雨中。
据说审理罗春一案件,签署一张张处决令,于沐之县长几度落泪,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同志一个接一个的冤死,但是迫于环境压力,他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建国后,傻二印曾找上级组织要求重查罗春一案件,把杨书记吓了一跳,“张飞鹏还有儿子?”
重查启动后,被问此案有无实据时,杨书记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没有实据,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夺人性命吗?杨书记对此振振有词:“但是因为一开始就用了肉刑,结下仇恨,如果释放,他很可能投敌。作为县委领导他投敌会给冀东抗战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处决他完全正确。”古罗马有“孤证不为证”之说,到了杨书记这里,连孤证都不需要就可定罪。
就这样,牵连了成百上千抗日干群的的所谓“汪派国民党”一案,重查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就给冀东这桩冤案打了封印,让数百条冤魂不得安息。
几十年后,潘家峪重现生机,村庄不再寂静,村民耕地造屋,不时会挖出白骨,却无从知道是谁的遗骸。张家也曾试图寻找张飞鹏张一民父子的遗骨,却无从查起。当年的行刑者都讳莫如深,对冤死者的亲属避之唯恐不及。有人说,那一带常发生灵异事件,能听见惨烈的哀嚎在山谷回响,声声凄厉,如浭水长流,绵延不绝。
作者简介:业余写手。冀东人。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3 小路(三十 )
- 浏览:52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1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6 樱花树下
- 浏览:46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3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39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290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8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35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7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89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4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49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4 换妻
- 浏览:16247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2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