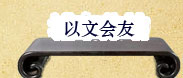内容
《浭水流》第一部第二十三章
《浭水流》第一部第二十三章 
纪实体家史小说《浭水流》第一部 抗战篇 血洒冀东
第二十三章 冤家路窄
走投无路的张达民决心重返抗日队伍,宁可被自己人冤死,也不能窝窝囊囊地饿死,更不能投敌。于是他就写信跟县长联系,可是于县长和继任者接连牺牲,丰润境内的整个交通线瘫痪,信根本送不出去。庆幸的是,青纱帐一起,日寇就在五月底结束了春季大扫荡。
然而当秋风吹萎青纱帐,日军又开始了更加残酷的秋季大扫荡,于九月中旬动用了四万多兵力,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对冀东反复清剿。从丰润县城到左家坞的三个炮楼,分别驻扎上百兵力,在披霞山脚下挖了深两米宽五米的隔离沟,切断进山道路。为落实保甲连坐制,各村都安排一个特务监督保甲长,每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如果有一人从事反日活动,十户同罪、百户受罚。以丰润到左家坞的公路为界,路西是日军,路东是伪治安军,一个村一个村的进行清庄。罗文口因在公路东,清庄的敌军主要是伪军,相对来讲,遭受的烧杀不似公路西那么严重。
在公路西侧,日寇实行“三光”政策,丰润县日本宪兵队长米谷是个杀人狂,尤其喜欢用刀劈人。清庄中宪兵队每到一地,都先用两桶凉水浸泡两把倭刀,那是九五式士官刀,微弯带弧度,寒光闪闪。然后胡乱从村民中拉出二十来人,跪成一排,只等米谷一到,就双手抡刀,让一颗颗头颅滚到地上、一股股血注喷到空中。如果一刀劈下去,没做到头颈分离,他就嗷嗷怪叫。
米谷劈人太多,没等大扫荡结束,就把自己劈疯了,半夜三更的跳起来,抡着战刀,像野兽一样吼叫,见啥劈啥。
听说王家哲从北平回来,达民去他家串门,二人聊到很晚,回家刚刚睡下,就听姐姐喊他快逃。淑敏的婆家,在吴事庄是大户人家,公公为人仗义,热心支持抗日,所以,冀东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周文彬每次都住他家,王家老两口也待其如亲子,再加上王志的四弟当了八路,王家在大扫荡中就成了清庄的重点目标,围吴事庄,淑敏就带孩子逃到罗文口,围罗文口,她再逃回婆家,就这么来回奔波。
这天孩子腹泻,午夜时分,淑敏带孩子上茅房,听到从西河沿传来吵杂的人声,急忙跑到弟弟房间把他叫醒:“快跑,肯定是鬼子来了。”
达民以为敌人从河西公路过来,就往村南跑,结果刚出村就见敌人从南面宋各庄过来,他只好淌水过河,到了披霞山,碰到躲藏在林子里过夜的哥哥和朋友,秋天夜里山风很凉,伯民和朋友冻得瑟瑟发抖。
“你兜里要是有钱,就买张车票去秦皇岛吧。”达民向哥哥提议,感觉这次扫荡会延续到冬季。
第一次清庄,伪军软硬兼施,哄骗村民说,“参加八路当村干部都是被蒙蔽,皇军宽宏大量,只要把武器的交出来,洗心革面,既往不咎。”
村民都被圈到南庙院子里,特务点名叫村干部出来,特务队长周学礼说, “别害怕,就是互相见见面,有枪的就交出来。”
头一个找的是化名国泰的于志波,恰逢国泰患疟疾,整个人烧得火炭一般,家人用门板把他抬来,周学礼见他半死不活的样子,就假装慈悲,说看着乡长李兰求情的面上,高抬贵手,“都病这样了,回去歇着吧。”
见此情景,胆小的李云就主动上前,“一时糊涂,当了八路的村干部,以后再也不做反对日本人的事。”
“好啊,痛改前非就好。”周学礼称赞。
慑于敌人淫威,又有几个村干部站出来表态,不是村干部的王家哲因为跟达民是好友,也被拉出来。表完态,特务们又逼迫他们高呼“皇军万岁”。
第一次清庄,国泰因病得福,毫发无损,却埋下后患,到了文革,被红卫兵认定是变节投敌,本乡一个叫李带的造反派怀着与叛徒不共戴天的仇恨,朝他猛踢,一脚踹中命根,“叛徒”当即倒地,再也没能起来。喊“皇军万岁”的几个村民,只有王家哲活到六十年代,成了被批专业户,每逢批斗大会,不管是批判啥,都被拉到台上,猫腰撅腚的坦白罪行,一直持续到批林批孔。
伪乡长李兰为人油滑,清庄过后就假装中风,坚辞乡长职务。过去的香饽饽,如今成了烫手山芋,谁都不肯接任。保长甲长三十多人,推来让去惹得驻村特务大发雷霆。就在僵持不下时,大嘴巴于令彻不知那根神经搭错、犯了官瘾,跑来毛遂自荐。
经过春季和秋季两次大扫荡,日寇在冀东制造了东西七百里南北八十里的无人区。抗日部队被迫扯到长城北,很多抗日干部逃往青龙县的山区。冬季到来,草木凋零,光秃秃的田野,没有任何屏障,无法开展游击战,冀东抗日烽火几近熄灭,很多群众失去了信心。就在严寒将大地冻裂的时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为了鼓舞士气,让群众知道抗日队伍还在抵抗,冀东抗日司令李运昌亲自带四个连到唐山附近召开乡长大会,动员军民坚持斗争。
这次大会,声势浩大,敌人听到风声,出动伪治安军三个团,将李运昌部围困在马家峪山上,日军放出系着劝降条幅的气球,数千伪军高喊着“活捉李运昌”,疯狂地向山顶冲锋。
被围困的李运昌站在山顶喊:“我李运昌就在山上,你们要是能活捉李运昌,冀东的游击战就不坚持了。”
见敌人迫近,县长高鸿劝道:“老掌柜的,你换便衣突围出去吧。”
李运昌说,“我要是换衣,以后还带不带部队?我宁可牺牲也不能换便衣。”
闻此言,众人肃然。就在大家决心与司令共存亡,决战山巅时,有个连长急中生智,提出一个方案,说我带部队主力向东突围,一个警卫排掩护老掌柜的从西杀出去。大家一听,都感觉这个方案可行。
突围成功。李运昌司令的安然脱险,给了敌后抗日军民极大鼓舞。
1943年农历腊月初四,县武装大队长王奎生,即化名雏燕的原泉河头区长从北口返回,满脸疲惫的找到村干部国泰说,“我累坏了,在这里休息几天,你们设法掩护我,。”
抗日队伍的内部清洗和鬼子的两次扫荡,让很多抗日群众动摇,国泰连找几个,都用各种借口推脱。他只好来找达民。
“区长需要掩护,可大家都被吓怕了,找谁都不敢出面,我实在是没辙。”
达民跟着国泰去见雏燕。
“没想到老罗的事把你也牵连了。”雏燕一声长叹。
“虽然不在队伍里了,区长你放心,张达民永远抗日。你就藏王恩照家的地洞吧,我负责站岗放哨。”
哨位在村西路口,两边各有一棵大树。翌日早晨,张达民刚到树前就看到特务骑着自行车下了公路,他转身就跑,找到国泰和区长,让他们赶快下地洞。
“你也下来吧。”雏燕说。
“我对王恩照不放心,怕他万一出卖你。”达民坚持要在外面观察情况,防止地洞的主人给特务报信。
把洞口伪装好,张达民就背了个粪筐从后院出去,刚出门就撞上两个特务。
特务拦住他问:“你咋不去听训话?”
原来敌人把村民都圈到村南南庙附近一个场院,听翻译官宣讲“大东亚共荣圈”。达民说我这就去。两个特务半信半疑地押着他走,走到十字路口土地庙,新任乡长于令彻迎面过来。
特务问乡长:“这人是你们村的吗?”
“是,当过八路军,现在不干了在家呆着。”画蛇添足是于令彻的一贯作风,这次也毫不例外。如果他仅仅是回答个“是”,达民也许就可以顺利走到南庙,混进村民中不被发现,他这么一多嘴,张达民插翅难逃。
“好啊,你还当过八路,绑上。”两个特务如获至宝,立刻用毛巾把达民的双手在前面绑上。
达民愤怒地瞪了于令彻一眼,懊悔儿时那次打架没一杠子把他砸死。脑袋少跟弦的于令彻,没意识到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既出卖了张达民也给自己挖了个坑。
张达民被押到南庙。冤家路窄,雨风穿着伪军制服斜挎着步枪、腰里还别着把手枪,耀武扬威地迎面走了过来。
“你还没死啊?”见到被捕的达民故作惊讶。
“我要是死了还能看见变色龙吗?”达民反唇相讥。
“我是变色龙,你就是丧家犬。你跟着共产党,给八路卖命,到头来咋样?差点被活埋。”雨风嘿嘿地冷笑。
“被活埋也强过三姓家奴。”达民啐了一口,心里暗想,之所以那么多人被活埋,还不是因为有你这种人。
“好小子,到这份了还嘴硬。”
恼羞成怒的雨风上来一拽,绑住达民双手的毛巾松脱,他接着把达民的胳膊往背后拧,却被张达民顺势一个转身、反手一托他的下巴。瘦小枯干的雨风被推了个趔趄,差点摔倒,气急败坏地掏出枪牌撸子指着达民:“我一枪崩了你。”
“你崩吧。”
达民见他的枪没顶子弹,就知道是虚张声势、没胆量私自处决要犯。枪牌撸子有两个管,上管缩进去是顶着子弹,两个管一边长就是没子弹。
鬼子翻译官听到吵嚷声走过来,雨风立刻胁肩谄笑,“这小子就是小张。”
翻译官一听是大名鼎鼎的小张立刻就说:“拉到那边去!”
“那边”是被拉出来的几个村干部和八路军家属。达民刚站定,一个穿呢子大衣戴礼帽的家伙就走过来:“你就是小张啊?认识我不?”
怎么能认不出?长脖子、高颧骨、两腮无肉,一双凶狠的三角眼。这张脸在家被抄的第一天就深刻在张达民记忆里。
“我姓周,叫周学礼,南李庄子人,丰润县特务队长,你们活埋了我爹和我哥,抓了我好几次,这回我站你眼前了,你怎么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张达民一声冷笑:“咱俩换个位置,这话我也会说。第一次带鬼子抄我家的就是你。”
“你小子死到临头嘴还硬,拉下去过堂。”周学礼一声令下,特务就把达民拉到隔壁农户院子里用刑。
一个特务拿了支鸟枪,抡圆臂膀,噼里啪啦的开打。
一下、二下、三下。
“村里有没有八路?”
“没有。”
“谁是村干部?”
“都跑了。”
一下,又一下,数着数着,忽然数不清了,也不再感觉倒疼痛,麻木感从局部扩大,蔓延到全身。咔嚓一声,特务手里的鸟枪打断了。
“这小子骨头真硬,枪都打断了还不说。”特务看着手里断成两截的鸟枪说。
“灌凉水,看他招不招。”在一旁叉着腰观看的周学礼下令。
于是就从河里担了一挑子凉水,从庙里搬出一条长凳,两个特务把张达民摁到凳子上,舀了瓢凉水,扒开他的嘴、往里灌。达民憋住气,不往下咽。凉水顺着嘴角流出,一秒……十秒……三十秒……实在憋不住才吞一口,就这样,灌了半天也没能击垮他的意志。
“妈的,我就不信治不了你。”周学礼又想出一条毒计。
不再灌水,而是用湿毛巾把张达民的口鼻蒙住,这么一来,他只要吸气,水就往鼻子里呛,不吸,又憋得胸腔欲裂。这招太毒了!疼痛可以凭坚强的意志抵抗,呼吸却不是主观能支配,血肉之躯不是铁骨钢筋,再怎么顽强也不可能超越人的生理极限。
死,对此时的张达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一秒一秒的坚持中,他在心里默念:快让我死,快死吧。
拷打是矛,意志是盾。如果让矛一直刺下去,再坚硬的盾也会刺穿。挺不住了,必须得想办法。灵机一动,他说:“你们带我到人群里去认,我去指认八路和村干部。”
“这小子,终于服软了。”
周学礼很得意,令手下把张达民从条凳上放下来,用绳索绑住手脚,扁担穿过去,由两个特务抬着去人群里指认。达民假装认真地察看,村民都很紧张,生怕他指认到自己头上。
“没有,一个也没有。”转完一大圈,两个抬扁担的特务累得直冒汗。
“这小子是耍咱们。”周学礼怒骂,“给我打。”
知道他的躯干已经被打麻,这回吊起来用三八枪打踝骨,那是他尚存痛感的部位。而且人体这个部位没有肌肉脂肪,神经对疼痛非常敏感,一下下击打如钢针猛刺。
“说。” ……
“说不说?”……
“快说!” ……
天空高远,目力所及,空空荡荡,像他的躯体,所有的意识都飞离,只剩下疼痛。我咋这么经打?打了这么久为啥不死?疼,太疼了,比子弹击中疼、比冰河里冷水冻的疼、比不打麻药做手术还疼。那些痛都有时限,挺一会儿就过去了,可这酷刑没有尽头。盾要被刺穿,死亡,却迟迟不来。还得想办法,得让盾得到修补。于是又生一计,他开口说道:“我想起来了,有个地方可能藏着八路,我带你们去找。”
“姓张的,你再怎么骨头硬,也是肉长的。”周学礼自鸣得意,命令两个特务跟着去找。达民把他们带到王玉普和邻居家的一个夹壁墙。这个夹壁墙他进过,知道那里只是藏着吝啬鬼的盆盆罐罐。
夹壁墙外面罩着厚厚的秸秆做伪装,特务命令张达民拆掉秸秆。双脚一触地,脚踝火辣辣的痛,用不灵活的双手,一根一根地拆秫秸,有意拖延时间。
“他妈的,你快点。”特务吼。
快不了,被打得半死的人想快也快不了,何况他不想快。拆了二十多分钟,终于拆完。
“你进去。”特务怕里面有埋伏,不敢进。
达民就进去,在里面磨蹭一阵,然后说:“没有,不信你们自己进来看。”
一个特务打着手电进去,发现果真啥都没有,气得大骂:“你他妈又耍了我们。”随手抄起一根木杠朝着张达民劈头砸下。达民被砸倒,头皮登时豁开一个口子,鲜血顺着额头流淌。
另一个特务见状就说别打了,再打就死了,咱得留活口。两个特务把张达民拽起来,又押回到场院,又推到那些蹲在地上的人群里。步履蹒跚、满脸是血的被这一推踉跄欲倒,幸而一双手将他扶住。透过被鲜血模糊的视线,看清是好友王家哲。
村子被围时,王家哲正在街上卖豆腐,挑着担子被抓来。
“这个卖豆腐的是村干部。”雨风信口雌黄。
倚着好友,达民瘫坐地上。雨风又走过来恐吓:“等会儿就把你们枪毙。”
毙吧,一死百了,不用再受折磨。从头到脚全身都在向大脑发射疼痛信号,有钝痛有刺痛有裂痛,有的痛成片,有的痛是点,有的痛是条索状。意识阵发性的混沌,混沌时很舒服,很惬意,真想就这么睡过去,可疼痛又将意识从混沌中唤醒。
“妈——呀——”院子里又传出惨叫,是村民小河春,不知为何也被雨风说成是村干部,正在受刑,打了一阵,特务累了到一边抽烟歇乏,小河春趁机挣脱捆绑逃走,朝村南被积雪覆盖的田野跑去。
冀东地区在夏天收割完小麦后,紧接着是种地瓜,叫麦茬瓜,秋天收获,储存在地瓜井里过冬,做为冬春口粮。地瓜井,一般有三四米深,一米直径,井壁留有便于蹬踩的脚窝。在罗文口村南那片地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地瓜井,井盖上盖秫秸保温。厚厚的冰雪,让井盖跟周围毫无二致。
小河春在前面跑,几个特务在后面追。过了场院,不远处就有一个地瓜井,小河春知道大概位置,绕了过去,后面的特务不知情,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咕咚一下掉到井里。后面的一看,就驻足开了枪,小河春中了两枪后又被拖回来。
特务们把同伙被摔死的怒气撒到小河春身上,把他也吊起来打踝骨。这下他扛不住了,乱说一通。于是,特务就把他说的人,一个一个从人群中拉出来。时近傍晚,敌人准备撤退,放了半死的小河春,把张达民等扔到马车上。
“谁是保长?”周学礼问。
按日伪“保甲连坐法”,特务要带两个保长一起押送县城。
迫不得已,两个保长挨挨蹭蹭地站出来,周学礼正要下令出发,一个老头上前说,“我是甲长,让我也去吧。”
还有自己要求去的,村民摇头叹息,特务们暗自发笑。
“你是甲长啊?那好,上车吧。”
老汉叫王占勋,根本不是甲长,他打诳语要求跟去,是因为独生子王恩景在车上,爱子心切让老人将生死置于脑后。
作者简介:业余写手。冀东人。
上一篇:雨后是彩虹
下一篇:晚风吹过白马坡(3)
发表评论


分享本站
- 年度作品榜
- 浏览:71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四
- 浏览:56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三
- 浏览:53 小路(三十 )
- 浏览:52 美丽的南斯拉夫(五十五
- 浏览:51 去红军苏区
- 浏览:46 樱花树下
- 浏览:46 红军游击队长肖明虎(十
- 浏览:44 八路军排长叶成德(三十
- 浏览:43 逆流之河:错位的救赎
- 浏览:39 美丽的南斯拉夫(三十八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3290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90088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935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97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689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314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349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20254 换妻
- 浏览:16247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
- 浏览:16222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