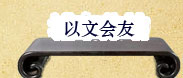偷袜子的人 
爸爸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是与妈妈离婚而离家的。
妈妈疲惫地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端庄白晰的脸上布满憔悴,她太累了。
“妈,妈,您别太难过了。”我小声地安慰她。
妈妈睁开眼睛望着我,说:“我不难过,就是累。”
“唉——”我叹了一口气,“您不是太难过就好,其实您并不老,今年46岁,按新的年龄划分法,才刚进中年。忘掉他,忘掉爸爸。”
妈妈脸上出现淡淡的难以觉察的笑容。我觉察到了。
“妈,人生不就那么回事么,想开了,什么都无所谓的。”我说。
“聪儿,一个未涉世的女孩子家,学那么世故干什么。”妈妈慢慢地说,似乎有点不高兴。
“你们五十年代和我们八十年代的人就是不同。”
“怎么不同?”妈望着我。
“没法说。保守,古板,说很实在吧其实又虚得很。”我很干脆地说出我真实的评价。
“还有吗?”
“嗯,对感情看得太重,也就是您们常说的执着吧。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说着,看了妈妈一眼。
妈妈没有言语。
我自顾自地说下去:“这也难怪,你们是看《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长大的一代。”
妈妈皱了皱眉:“那又怎样?”
“僵化呗。电视采访中,演《红色娘子军》的老演员自我感觉那么好,新演员就不习惯了,说那些动作表情,不是攥拳就是瞪眼,真让人受不了。”
妈妈有了一丝笑意。
我越发大胆了,滔滔不绝地往下说:“那《白毛女》中的喜儿也忒傻,爱什么大春哪,嫁给黄世仁多好,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老爹也不会死。”
妈妈满脸惊异问道:“你这么想的?”
我一愣,忙说:“不,是我们同学说的。”
妈妈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你们可以看《泰坦尼克号》了。”
“那又怎么了,《泰坦尼克号》还不是老头子编的,我们同学说那里面的露丝也够可以的,干嘛不和卡尔好,卡尔那么富有,即使不爱他也可以和他先结婚,再与杰克一起玩。最后离婚还可以分得卡尔一半的财产。”
“别说了!怎么讲实惠讲到这么庸俗的地步?”妈妈真的不高兴了。
“妈,这都是我们在一起说着玩的,您别当真啊。”我赶紧解释。
“不用解释了,也许你不会这样想,你们这一代人肯定有不少这种想法的。真是可悲。”
“妈,其实你们这一代也不全都一样。您看爸爸如果不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欢乐,也不会离开您离开这个家的。”
“这倒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不同,思想本质不一样。我希望你能象我。”
“妈,我当然像您啦。不光长得象,也有一点您的气质,是吗?”我轻轻地搂着妈。
“可思想不象。”
“那很正常啊,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嘛。在你们那个年代,太痛苦了。”我总免不了快嘴快舌。
“是啊,痛苦。”妈似乎在小声地自言自语。
我看到妈的那种沉思的样子,不禁心里一动,问道:“妈,您在和爸结婚以前还有过初恋吗?”
妈沉默不语。
我说:“不作声就是默认。”
妈淡淡地说:“我们那时候的事,你不会懂的。”
“会懂的,会懂的,”我连忙接过话头,“妈,给我讲您的故事吧。您遇见过谁?他是什么样的人?”
妈看看我,若有所思。我急切地说:“我一定会理解您的,就算给我上课,好吗?”
“傻丫头,上什么课?”妈说,“我边想边讲,你不要打断我。”
我老实地坐在妈的身边,她开始了回忆……
三十年了。下农村时,我才刚刚十六岁。我们四个要好的女生组成一个知青组,随学校统一安排在富饶而又贫困的荆州地区。说它富饶是因为这里地处江汉大平原,赫赫有名的鱼米之乡,说它贫困是由于在绿竹掩映之中尽是破烂茅屋,农民们身上衣裳口中食都难以为继。说来你都不信,用进口的化肥包装袋做衣服的竟是一种特权和时髦,有一首顺口溜这样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要问干部啥模样,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好了,别笑了,你们是很难以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
我们四个女生就是我曾给你常提到的张阿姨、李阿姨和许阿姨。当时下乡时,学校规定自由组合,男女生搭配,同班的男生和一些高年级的男生都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建组,被我们拒绝了。一方面是我们相当自信,自信不依靠于男生,自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幼稚的骄傲。在学校时,我们是全市中学生最大的造反组织“红卫兵团”文艺宣传队的,我们四个人被誉为学校里的四朵金花。你张阿姨身材高挑,能歌善舞,是宣传队里的台柱子,被男生们称为“芍药迎风”。你李阿姨一副林黛玉的模样,一手琵琶弹得出神入化,男生们称她“梨花带雨”。你许阿姨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可与男生打成一片,颇对男生的味口,他们都叫她“海棠醉日”。你一定要知道我的美称吗?不说了吧,挺俗气的。好吧,他们说我有“政治头脑”,还有一种贵族气,所以称之为……“牡丹初绽”。很难听是吧?那个时候么……
农村就是农村,尽管我们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完完全全的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使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天真,那“革命造反”的浪漫和载歌载舞的喧嚣对我们来说,真是恍若隔世。幸亏周围队的男生常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否则真不知日子该怎么过。冬季的农活主要是修水利,也就是挖河挑土,最单调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这活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也不知最后挖出的渠道有没有用,那时农民的劳役是无偿的,无用的工程连“学费”都不用出。在水利工地上,中午宝贵的休息时间使各队的知青们聚在一起,我们憩息的地方往往最热闹,老远就可以听见说笑声。
一次,我们带到工地去的腌辣椒引起大家的味口,二队三队的知青都来“共产主义”。一位比我们高两届的男生说:“‘四朵金花’到底不简单呐,连腌的辣椒都可以招蜂引蝶。”大家都笑起来。
小许满脸通红地说:“那好,以后我们都去吃你们的。”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几个男生异口同声说。
又是一阵笑声。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说老实话,这个地方的土壤不适合我们的‘金花’生长。这铁锹可不是琵琶。有诗为证:芍药迎风风欲摧,梨花带雨随雨落,海棠醉日日无情,牡丹……”
“停!”我大叫一声,“不许再这么叫我们了。亏你还是高中生,一副小资产阶级情调,酸溜溜的。”在“老三届”中,高中三届初中三届,我们初中六八届是最低的一届。其实,我这么说是强词夺理,只是不想让别人说我罢了。
大家也不在意,笑笑也就算了。小许利嘴快舌的与他们打起了嘴巴官司。
突然,我发现在不远的土坡上有一个知青躺着看书。他一手枕着头,一手拿着书,样子倒潇洒得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农民扎堆,知青扎堆,他为什么特立独行?我有些好奇。
“他是谁?”我指了指土坡,问“眼镜”。
“他你都不知道?学校‘造反总部’的‘黑高参’柳涛,号称‘柳克思’”“眼镜”回答。
哦,是他,我有点印象了。学校里的‘红卫兵’头头,也就是学生领袖,我大都认识,这个人知其名而难见其人,他不太喜欢出头露面。运动后期好象脱离组织,成了“逍遥派”。“他在你们那里吗?”我又问“眼镜”。
“是呀,最近出了一个丑闻。”
“丑闻?什么丑闻?”我惊奇地问。
“他偷袜子。尼龙袜子。”“眼镜”神秘地说。
你别笑,在六十年代人们穿的是布袜子或线袜子,尼龙袜子很昂贵而且是时髦的。穿尼龙袜子就象九十年代初,手持“大哥大”可显示人们身份不凡一样。不过我当时还是感到不理解和好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何况还是袜子?!
“真有这事?”我问。
“我也是听他们讲的。”“眼镜”有点支吾。
我摇摇头,不太相信。但对这位“柳克思”心存一种疑惑:他是个什么人?
在六十年代后期,“早请示,晚汇报”是一种可笑的时尚,最初是被专政对象被迫的“赎罪”形式,后来竟然异化为所有的人们对毛泽东表示虔诚的必须方式,从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直至军营,莫不盛行。那种仪式是绝对严肃的,在早餐前或是开工前,所有在场的人面对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立正站好,这时由一个人声音宏亮的开头:“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大家一起喊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开头人又说:“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大家又一起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个仪式完成后,才能进餐或开工。蛮好笑,对不对?可那时候谁也不敢马虎,谁如果不恭敬或是表露抵触情绪,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意味着将打入社会的十八层地狱。
有一天早上,我们按惯例做着“早请示”。“万寿无疆”一喊完,就听见身后“哈哈”一声笑,接着是一句惊叹:“多么虔诚的善男信女呀。”
我们惊异地回过头去,看见一位个子高大的男生靠在门边,脸上带着微笑看着我们。小许马上叫道:“好哇,柳涛!你竟敢讽刺我们,太反动了。”
“哦,我说什么了?我是来借铁锹的。借不借?”他依然面带笑容,只是向我们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
我怔怔地点点头。他拿起门边的铁锹,招招手就走了。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不知说什么好。小李说了一句:“他真大胆。”不过,他的话给我们一种新鲜的奇怪感觉,我们当时不能说他对,也不能说他有什么错,只觉得那一句玩笑话有无尽的寓意。
有趣的是,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提起做“早请示”,似乎大家都忘了。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说起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触——别瞎说!哪有什么“亲密接触”,你们都被痞子蔡给教坏了。我们那个时候,个人生活都是很严谨的,就象人们比喻的“古典小说”,翻了一百页男女主人公的关系都未确定,不象“现代小说”还未到第二页,男女主人公就上了床。说正经的,那天我挑着一担碾好的米从镇上回队,因为求近,我选择了河边的一条小道。那是一条很秀丽的河,河水静静的流淌,河面的波纹犹如变幻不停的图案,毫无一丝喧嚣和嘈杂。河的两岸是一大片青沙河滩,种着一片绿盈盈的花生,河滩边上是一排排高大的杨柳,再过去就是随着河道蜿蜒的大堤。我太欣赏那片美景了,以致于对道上的小沟竟视而不见,当我一脚踏进去时只来得及大叫一声。我跌倒了,脚崴得厉害,脚脖子立刻红肿起来。我揉了揉,根本与事无补只给我带来几声痛苦的呻吟。我只得四处张望,盼望上天有眼。
奇迹居然发生了。我看见堤边走过来一个人,知青模样。对,是他,是柳涛。他走到我跟前,既不帮我挑担,也不扶我,而是站在那里问:“你怎么了?”
“你没看见我脚崴了吗?”我坐在地上没好气地说。
他笑了笑,说:“我好象听说哥白尼因观察天象而掉进沟里,你也是这样吗?发现什么了?”
“发现个鬼,他见死不救!”
“哈哈哈哈!”他一阵大笑,一手将我扶起,一手将箩筐轻易地上了肩,说“我们到堤边去吧。”
在堤边,他从一个黄书包里拿出一个小铁盒,铁盒里面装着药棉和几支银针。
我问:“你还会这个?”
“偶尔有点兴趣。你怕不怕?”他拿出一支约两寸长的银针,看着我问道。
我迟疑点点头。
他动作麻利地在我脚脖处进针,不停地捻动,一阵阵酸麻触电感使我不自禁地呻吟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拔出针又使劲在患处揉捏了几下,对我说:“站起来试试。”我站起来试着走了两步,虽然还有些隐痛但走路是没问题了。我不好意思的说了一声谢谢,他不在意的说:“歇会儿吧,待会我收工时顺便把这担米送到你队里。”其实,他们队和我们队虽隔不远但方向不同,并不顺便。
“你在这里上什么工?”我感到有点奇怪。
他指指那一大片花生地问:“那是什么?”
“花生地呀。你考秀才呢?”我怕他要笑我五谷不分,认不得花生。
他笑笑说:“我是来看花生的。”
“看花生?”
“是呀,我这么大的个子,挺吓人,是不是?谁要偷花生恐怕是要过我这一关了。”
还有这种美差,我心想。农村的体力活是很苦的,不干活坐在这里还记工分,太舒服了嘛,比现在看大门的“保安”还舒服。
他好象看出我心里的活动,接着说:“这里有来偷花生的,无非是周围村队的人。你想,如果是本队的老乡坐镇此地,那他遇见的不都是熟人?甚至有不少沾亲带故的。他若管吧,抹不开情面,农民最讲情面,不管吧,又丧失原则,拿工分有愧。所以派一个知青外乡人来,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农民有农民的聪明,不然伟大领袖为什么叫我们到这里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他说得很有道理,我心中暗暗佩服。这时,我才注意到草地上有一本厚厚的精装书,这肯定是他带来看的。我伸手将书翻开,书名是《印度的发现》,作者尼赫鲁。我感到十分困惑和不安,在那个时代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书,在政治与文化领域里就几乎没有可阅读的书,一切作品都划归“封资修”。我依稀记得,这个尼赫鲁在64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时正是印度总理,是反华的。他怎么看这种书?
“这书讲的是什么?挺反动的吧。”我希望他认可我的话,这样我就可以为他在心里作某种解释。
谁知他说:“这是尼赫鲁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识和感受,无所谓反动不反动。写得很不错。”他看看我的表情,又说:“我们换个话题吧。你喜欢看书吗?”
我连忙点点头。
“你看过些什么书?”
看过什么书呢?我努力搜索自己的记忆。除了小学和初一(读完初一就停课闹革命了)的课本,我看过的一些书如《水浒》、《西游记》,那是“封建主义”的东西,《红岩》被说成为叛徒涂脂抹粉和翻案,《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被打成“五一六极左分子”,连《雷锋的故事》都被指责为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我踌躇了一会,突然想起一本书,不由说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啊,里面有个冬妮亚,和你一般大,对吗?”他笑着说。
我脸红了,我喜欢冬妮亚,但口里却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富人。”
“但她一直喜欢保尔,在关键的时候掩护他并且救了他。很有性格,这就够了。”他洒脱地挥了一下手。
我想辩驳什么,但他说到我心里去了。
“哦,对保尔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书,还记得吗?”
“好象是《牛虻》。”
“你看书很仔细。看过《牛虻》吗?”
我摇摇头。
“很可惜。”
“那你跟我讲讲吧。”我有时和小孩一样,有喜欢听故事的天性。
“我可没有讲故事的才能,只能告诉你一个故事的线索。有一个出身贵族的单纯青年,参加了一个秘密革命党。由于一次情感的忏悔暴露了组织的机密,结果遭到他深爱的女友和同志们的误会。他无法解释,只有使自己在他所熟悉的环境中消失。十几年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思想敏锐而惊世骇俗的神秘人物,绰号叫‘牛虻’,他受到下层人民的爱戴,积极组织反抗压迫的起义。他写的文章辛辣而深刻,在当时的报纸上纵横挥洒,引起社会轰动。谁都知道他,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那他原来的恋人知道他吗?”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她猜疑但不敢确定。”
“后来呢?”我有点迫不及待。
“后来嘛,你自己去看吧。只有自己看,自己体味才够劲。”他嘴角现出笑容。
“那么你从这个‘牛虻’那里体会到什么?”
“残酷。”他冷峻地回答。
“残酷?”
“我是说他对自己是残酷的。他永不原谅自己。”
我似懂非懂地望着他。发现他的头大,眼睛大,嘴巴也大。眼睛常带一点眯缝,而嘴角总是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他觉得我在看他,就说:“看什么,太阳快下山了,回家吧。”
我说:“又有人偷花生怎么办?”
“偷就偷吧,生活困难免不了偷。我要向他们宣布,你们偷的是资产阶级的花生!”说着,他做出电影中列宁的姿势。我大笑不已。说实话,我当时觉得他“酷”极了,真的。
从那以后,我们的往来多了起来。有时候我到他队里去,有时他到我们队里来。每次来他都会带几本“禁书”来,所以很得大家的欢心。要知道在农村时,我们不光缺乏口粮,更缺乏精神食粮。生活的严酷使我们逐渐成熟,而偏僻的地域环境却使我们的思想有机会一点点地冲破樊笼。那时候知青中最流行的歌是《外国民歌两百首》,其中不少是世界上的名诗名曲如歌德的诗、舒伯特的小夜曲等,我们不仅是欣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歌曲中求得安慰,寄托憧憬,甚至寻找发泄。在那个时代这统统算“黄色歌曲”。对于封资修的“禁书”,我们简直是如饥似渴,我们看的书太少了。
有一天晚上,柳涛又带来一书包书。我们打开一看,有托尔斯泰、雨果等一大批名人作品,丰富极了,于是爆发了一阵小小的欢呼。我惊喜地问:“你哪里弄来这么些书?”他嘴角又现出那种微笑说:“反正不是偷的,不是抢的。算是救下来的吧。”
“什么意思?”小许紧盯着问。
“你们还不知道?校革委会成立的时候,你们初中的一个小将提出来,要将校图书馆进行彻底清理,把除了马列毛主席的著作及数理化的书籍外的一切书籍放到操场上烧毁,搞一个誓师庆祝大会,并声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焚书创举。当时教师代表坚决反对,但他们没有多少发言权,权力大多在学生手里。我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说这些是文化遗产,他们完全听不进去,说什么封资修的遗产就得砸烂就得销毁。没有办法只有使出最后一招,对于这些‘毒草’我们‘造反总部’将实行彻底的革命大批判,在分析批判过程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和破坏!就这样将书籍封存起来,阻止了一次愚蠢的行为。后来,下农村时,那一拨小将还未走,怕他们又搞什么过激的行动,所以就带了一部分下来‘继续批判’了。”
“那下乡这么久了,我们怎么不知道?”小张问。
“还不是怕你们也要‘焚书坑儒’,初中生比高中生更革命些嘛。”他笑着说。
“德性!”小许白了他一眼。
“我说啊,你们搞的这一套也就是以毒攻毒。不过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我沉吟地说。
他赞许地对我笑笑:“你,有头脑。”
小李拿起一本书,说:“瞧,还有这种书名的。”书的封面上印着《不是为了面包》。
“好看吗?”小许问。
“书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要丰富自己就得什么样的书都看一点。毒草也不例外。”他说。
“那你说文学书籍哪些比较好?”小李问。
“当然是名著好。我个人认为,俄国作品的思想性比英法美等作品更显得厚重一些,如托尔斯泰、屠格列夫、陀斯妥也夫斯基、普西金、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等。到苏联时代,这是一个新的专政时代,和我们比较切近,中国和苏联是一脉相承的嘛。我们不光要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战争作品,还应知道另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有位叫柯切托夫的苏联作家,有几部作品比较有名,在斯大林时代是《茹尔宾的一家》,赫鲁晓夫时代是《叶尔绍夫兄弟》,现在也就是勃列日列夫时代是《落角》。《不是为了面包》是杜金采夫的作品吧,写的是一个发明家到处碰壁的故事。他们不同程度的反映了一些客观现实,而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苏联文化方面管得严,但比我们国家好象还是强点。至少他们还保留古代的东西。”他侃侃而谈,我们都听迷了。
我们似乎还有许多问题想问,却又不知问什么。他看看我们说:“明天还要上工,不耽搁你们休息了。”说着,背上书包就出了门。
他走后,大家情不自禁的议论起他。小张说:“他懂得真多,我觉得他有种魔气。”小李认为:“他读了那么多书,但一点也不呆。”小许笑道:“我看呐,他是个大滑头。他丰富得象面包,长得也象。我们以后就叫他‘面包’吧。”“对,柳涛面包,挺押韵的。”大家嘻嘻哈哈的说笑着。
我没有作声。我在想,在同学中我一向是以博览群书而自傲的,在他面前怎么就显得那么无知和幼稚,他比我大五岁,比我高五届,也许这就是答案?
又有一次,公社在谷场放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这是件稀罕事,是绝无仅有的一回。那时候基本上什么电影都不许放,只有《新闻简报》。这部影片是很富有感染力的片子,看完后人们特别是知青还沉醉在剧情之中。我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柳涛,他默默无语不象很兴奋的样子。我对他说:“苏联功勋演员的演出就是不同凡响,他把列宁真是演活了。”他点点头,说:“是演的不错。但也有问题。”
“问题?什么问题?”我大惑不解。
他看看周围没有人,就对我说:“这是一部美化斯大林的片子。片中把斯大林描绘得与列宁非常亲密,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有所看法,这在列宁的著作中已反映出来。马克思与恩格斯既是事业上的战友,私人之间也有着崇高的友谊。列宁和斯大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里面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把布哈林描述成暗害列宁的帮凶,这就是捏造了。这部电影出笼于苏联大清洗的时候,值得深思。”
我不大懂他讲的内容,只是呆呆的望着他,觉得他深不可测。
“我说的话,不要对别人讲。明白吗?”
“嗯。”我认真地点点头。内心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被信任的幸福感。
城市要招工的消息传到了农村,在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知青们心情激动的盼望着这一天,那时这是知青改变自身环境的唯一出路。这一天来了,招工的师傅到我队了解情况,并和我们见了面。他对我们四个女生极感兴趣,还承诺一到厂里就让我们进厂文艺宣传队,参加排练样板戏。弄得我们大家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有种临战前的紧张。这时,我极想见到柳涛,极想和他作一次倾心的长谈。那天晚上,一扔下碗我就打算出门。我拣起几本书塞进书包,对她们说:“我到三队还书去。”小李问:“你一个人去?”小许接着说:“是去找柳涛吧。”我支吾了一下:“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为了面包!”她们后面异口同声地说,接着都笑起来。我一跺脚跑出了门,心里骂道:这些鬼丫头,心眼就是多。
我到他们队里已是掌灯时分。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废旧的仓库里,门半开着。我从门边看进去,他坐在一张破桌子前,在马灯昏黄的光线下专心致志地看着书。我想进去,却又想静静地观察他。于是悄悄地站在门外边瞧着他。
不知那是一本什么书,厚厚的象砖头一样。他手托着下巴,象一尊塑像。突然他抄起笔在书上迅急地写着什么,大概是在作他认为重要的批注。一会儿,他放下笔,轻轻的摇头,嘴里嘟噜着:“不对,不应该是这样……”过一会儿,他又轻声嘀咕:“很好,绝对是真理……”就这样他边看边写边说……
我不知在门边站了多久,心里洋溢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情,不由重重地喘了一口气。
他抬起头,见我在门边,叫道:“进来呀,站门口干什么?”我走进去,说:“我来还书。”他不言语,只是侧着头看我,嘴角又现出那种嘲讽的微笑。
我低着头说:“招工的已到我们队了,可能我们很快就会抽回城了。”
“我已经听说了。回城,好哇。知识青年到农村大有可为吗?否!在现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农村没有希望,知青还会有什么好命运吗?更何况他们头上还有一道‘接受再教育’的咒符。而一旦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根本变革,农民自身就可以创造奇迹。”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着,“就拿你们来说吧,四朵可爱的小金花,真是天生丽质啊,聪明而又有天赋和才能,如果象报上说的扎根农村,你们的前景是什么呢?不过又多了几个为了鸡和猪与邻家大吵大嚷的农妇而已。你说是吗?”
我被他说笑了。他看问题总是尖锐得不合潮流,但又是无可辩驳的。我猛然想起他的境地,问道:“你呢?你这次走得了吗?”
他的脸一片肃然,说:“不知道。我想,不会那么顺利的。”我的心也跟着沉重起来。
他叹了口气,对我说:“天不早了,你该回家了吧,还有五、六里地呢。”
我有些不舍站起身来。“我送送你。”他拿起我的书包。
“不用。”我言不由衷地说。
“客气什么,走吧。”
外面月光如水。田野似乎安睡了,几声狗吠,更显其幽静。
我们在路上闲扯着队里的事和知青的事。眼看就到我们的村头了,我想说的话还是没有说出来,憋得难受极了。
我停住了脚步。“怎么了?”他问。
我猛地抓住他的胳膊,颤声问:“你说,我将来能和你在一起吗?”
一阵沉默。
“我懂得你的意思。我比你大五岁呢,怎么会不明白呢?”他郁郁地说,“你就要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了,你的眼界将会更加扩大,你会遇到很多新的人,你会有很大很大的选择余地,我是微不足道的。你现在不懂,将来就会明白的。”
“不,不会的!”我带着哭音说。
“再说,你是高干子女,运动后期你父亲就有平反的可能,你的厄运就会彻底结束。而我出身于资本家,无反可平。在我们国家,家庭问题就是个人问题。难道我还去拖累你吗?”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诚挚溢于言表。
他说到一定深度了,我却一点也听不进去。
“最重要的是,我在人们眼里是具有危险思想的人。将来沦为苦役犯也说不定。”他露出一丝苦笑。
“如果你是苦役犯,那我就是玛丝洛娃。”我泪流满面地说。不知怎的,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竟用于自比,并且脱口而出。
“别这样,啊?你号称‘牡丹’呐,花中之王……”他象大哥哥一样哄我,“让我们握手告别,好吗?”说着他伸出手……
我摇摇头,哭着朝我的住处跑去。进屋之前,我朝村头望去,他还站在那里……
“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再也没有见过面。”妈妈眼圈红了,闪着泪花。
“那后来呢,他到底抽上来没有?”我关切的问。
“后来,听说他抽到地质队,从此浪迹天涯,不知所终。我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一点消息。算起来,他现在也有五十多岁了。”妈妈感慨地说。
“我很感动,真的,你们这一代人呐,都是理想主义者。”
“你还是不能真正理解。现在的女孩子呀,要么崇拜高仓健式的成天板着脸的木面男子汉,要么垂青满脸谀笑有钱有势的‘黄世仁’。”妈摇着头,不屑一顾。
“妈,那是别人不是我。”我急急地申辩,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那他偷过袜子吗?”
妈淡然一笑:“傻孩子,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邻队一位女知青从城里回来,给他们队知青带了一包城里的日用品,无意中将自己的一双花尼龙袜也塞了进去,柳涛将袜子拿出来放到床头,准备请同学带过去,不意后来被‘眼镜’看见
,到处做文章。‘眼镜’在学校时就嫉妒他,这不是秘密。”
“真无聊!你们这代人中也有这种人。”我气愤地说。
“好了,不说这个了。聪儿,你就要大学毕业了。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在个人问题上,妈也相信你的眼力,我只给你两点忠告,第一要找一个你爱的人,人是要讲一点精神的。第二不要相信甜言蜜语,没意思的。”妈恳切的望着我说。
“我知道了。我呀,一定找个笑傲江湖的令狐冲。”我调皮地说。
妈笑了。她有些疲倦,慢慢地闭上眼睛,沉浸在她沉重的梦乡之中……
是啊,在当代,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问题。我一点也不乐观的想着……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161388 武警战士陈开(一)
- 浏览:89901 武警战士陈开(四)
- 浏览:33584 南京大屠杀(四十二)
- 浏览:28622 第四章: 张桂花偷情被
- 浏览:27176 出轨(短篇小说)
- 浏览:26129 武警战士陈开(三)
- 浏览:24165 一个儿子五个妈妈的故事
- 浏览:19936 换妻
- 浏览:16189 路 第二章疯狂的八月
- 浏览:16160 美丽的乌托邦《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