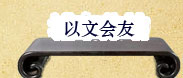苦木沟 
每当翻开过去保留下来的那本“诗词习作”笔记,看到里边那首《七律·枯木沟》时,我的思绪就会即刻飞到那个偏僻而又充满危机的山沟里去。
七律·苦木沟
冷月西山豁崖下,银河一线悬头上;
飞雪采坑踏瞎跑,骤雨危壁冒倾塌。
脚下暗穴不时陷,高空飞鸟惊啼远;
冬夏倦影斯犹在,岂叫片石染圣台。
——2010年初夏
诗题所指的“苦木沟”,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山沟。它地处太行山脉中段的东麓,蜿蜒于山峦之中,和无数的山沟一样,自山上向山下弯弯曲曲的延伸而去,形成了一道狭长的小山谷。相传这里早先曾长满了苦木树,故此而得名。不过现在早被这山里特有的核桃树和柿子树所取代了。
这苦木沟又是一道饱经沧桑的山沟。这是缘于沟内有一条横穿而过的铁矿脉。铁矿脉就生在沟里的半山腰间,它顺着山峦的走势呈条带状分布并出露于地表,其状呈直上直下的形态一直向地下扎去。大概是这里的矿脉出露的较好的缘故,因而这里过去开采的最为严重。从地表上看去,凡采过矿的地方,现在依旧裸露着一道道白花花的山体,寸草不生,与周边绿草如茵的山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它宛如一道撕开的裸露着白骨的伤口,正在滴着血在那里诉说着什么;远远望去,犹如一条遍体鳞伤的巨蟒,正卷曲着身子在那里喘息着、呻吟着。据说这里地下的铁矿也基本上采完了,最深已采到地下200多米的地方。不过在地表上所能看到的,只有几个废弃的一眼看不到底的黑洞洞的竖井口。
虽然这里的铁矿脉已经开采的千疮百孔,所剩无几。但当时铁矿石价格不菲,为逐利而不惜冒险的人,最终还是把目光盯在了这里。由此才有了一段我和同事们在此患难与共的不寻常的经历。
采矿的人就要来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监督采矿方把采下的矿石,保质保量地送往距此20公里以外的我们供职的公司里去,供给公司的选厂加工铁精粉之用。承担这项任务的人员,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早在此“看山”的我们这“三老一少”的身上。三老者,马老师、张工和我,都已过“知天命”之年;一少者,小王司机是也,他正值“而立”之年。马老师曾在煤矿学校任教,因此人们都对他以老师相称。张工是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俩都是文化人。巧合的是我们仨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都是在原单位“内退”后,外出打工到这里来的。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相聚共事,也是一种缘分。
2009年的冬天到了。采矿的人终于开着挖掘机浩浩荡荡地进山了。那笨重的履带式挖掘机,伸着长长的前臂,上面的挖斗像只大手一样向回勾着,只见它吱吱扭扭地爬行在崎岖的上山路上。在它的身后拖着一道长长的飞扬起来的尘土,恰似一溜黄烟一直飘到苦木沟的半山腰上。一时间,这山沟里响起了震耳的隆隆炮声,荒凉的山野原有的寂静被打破了。此后这炮声不时地在山野里回荡,不几日,这里就大变了模样。靠近矿脉的山体被扒开了,矿脉上尘封已久的覆盖层被掀去了,一条黑黝黝的40多米长,4~5米宽的铁矿脉暴露在面前。用磁铁一触,只听“啪”的一声,就吸在上面了。
矿脉被扒开后,两侧的山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狭窄而陡峭的大豁口。大豁口的底部自然是矿脉,在矿山上称这样的底部有矿脉的大豁口为坑道。要想进入到这条狭长的坑道里去采矿,只有通过开在一端的一个“马道”口进出。进到里边,所能看到的,除了脚下的矿脉和两侧陡峭的绝壁外,再就是头上的“一线天”了。在坑道里,靠山体外侧的峭壁尚不算高,而靠山体内侧的那面峭壁则足有30多米高,它纵贯整个坑道,并且几乎是直上直下地竖立在那里,令人望而生畏。按规定必须要把这高高的悬崖峭壁处理掉以后,下面的坑道里方可采矿。但是,采矿方为了一时省钱和尽早获利,竟然就这样在不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就开始采矿了。
当采矿方在坑道底部的矿脉上第一次打眼爆破后,被炸成大小不等块状的乌黑的矿石,铺满了整个狭长的坑道,但同时也意外地发现了在铺满坑道的矿石中,却掺杂着一定数量的矸石。原来这矿脉中含有矸石夹层,这样在爆破下来的矿石中,就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一定数量的矸石了。
“老王,你们要先把混在矿石里的矸石检出来,才能装车。”我对采矿负责人说。我尊称他的姓氏,其实他比我小十几岁。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是那种精明干练的人。
“那不粘,俺们也不是在一个地方采过矿,从莫听说过,崩矿以后还往外捡石头的哩;矿石、矿石,就是有矿也有石头,哪有露天采矿莫石头的哩?不管在哪都是一块装车。”他态度强硬,操着浓浓的当地口音回答。
真是岂有此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矿石说的是有矿又有石头呢。哪有这个理?矿石就是矿石,石头就是石头,怎么能混在一起装?公司要的是矿石,不是石头。”我太了解矿石中掺有矸石或其他杂质时,对选厂有多大影响了。其实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用选厂厂长们常说的一句无奈的话,就是“从河沟里拉一车河卵石来,再艺高的人也选不出铁精粉来。”想到这些,我接着以不留余地的口气继续说道:“你们在别的地方怎么装矿,跟这儿没关系;在这儿装就得把矸石检出去。要不我们不在发货单上签字,你们就是送到公司去了也没人接收,不信就试试。”一阵久久的沉默、无语,双方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档口,站在一旁的马老师开口打破了僵局。他用诚恳又温和的语气对采矿负责人说:“这是公司里的规定,不光是对你们,就是公司内部的矿山也是这样;不信,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再说,这事俺们就算不管,你们把混着矸石的矿石一块拉过去,到时候公司也会发现;那时莫说不收,就算能收下,起码也得扣吨。到了那个份上你们可就更不上算了,还显得不好看,俺们也跟着没法交代。”马老师是本地人,此前他曾在本县和乡里工作过多年,他知道怎样和这儿的人打交道。大概是看马老师是本地人,相信他抑或认为他说的话在理的缘故,最终采矿负责人别无选择地接受了我们的正当的要求。
在和马老师相处的几年中,他总是不漏声色地在关键的时候帮我一把。半年前,公司实行轮流值班。当月马老师按规定休假,这时公司领导安排我考察附近的一个竖井开采的铁矿。在找不到合适人选帮忙的情况下,我只好求助于马老师。他明知下这一带的竖井有危险,他也完全有理由和各种不失体面的说辞来推辞掉,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毅然决然地陪着我,靠手抓着提升钢丝绳、脚蹬着提升矿石用的吊桶的桶沿,就这样晃晃荡荡地连续下了两个300米深的竖井。最后我是完成了领导交办的考察任务,但谁会想到,这任务是在休假回家的马老师冒着生命危险、并不图报酬的无私帮助下才完成的呢?
大概采矿负责人没有想到,我们几个老家伙,又是“文化人”,竟然敢下到峭壁有坍塌危险的坑道里去;而且还一直站在挖掘机前,监督着挖掘机在扒矿的同时,把发现混在里边的矸石一块一块地检出来。也许他更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装矿的全过程中,一刻也不离开坑道,直到把整个坑道里的矿石装完同时把发现的矸石检出来为止。他大为惊讶和不解:一个打工的人,一个个又都这把年纪了,头头又不在这看着,这是何苦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他站在岸边,看着坑道里的这一切,面带愠色,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但最终他还是憋不住了,便冲着我们冷冷地喊道:“゙嗨,你们离勾机的挖斗远一点,这个铁家伙可不是闹着玩哩,稍微扫一下就了不得。碰重了,说出来不好听,可事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当下难受一下,下来什么也就不知道了,那倒不受罪,这还算好的。就算碰轻了,少说也得弄断了胳膊腿儿什么的。虽说现在能换假肢了,可再怎么说那也就不方便了。到那会儿就是想出来打工,也就莫人要了。人都是这样,你能干的时候,有人拿你当回事,你要是不能干了,就莫人搭理了。最多当下多给点补偿费,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看看你,可时间一长就忘了。到那个时候谁也就指望不上了,等钱花完了,只能拄着大拐在家门口找个看大门什么的活儿干,混口饭吃。可那也得有人看个面子才粘,要是莫人,谁会用你?但不管怎么说,个人只要能动还受不了大罪。怕就最怕伤着了腰椎神经线,那可就惨了。不说别的,就是老板多给出点钱,那是小事;个人躺在床上动又动不了,死又死不了,活受罪是大事。到了那会儿,甭说别人,连老婆也就不待见了。唉,都五十出头的人了,年纪说大也不算大,可说小也有一大把了。出来打工为挣点钱,安安全全的比什么不好,要是有个好歹,那可就犯不着了。”他这一番带血腥的残酷的恐吓性的描述,其用意非常明显。其中也不乏包含着他开始无奈地接受我们对捡矸石要求的怨恨。他的话显然话中带刺,但又不好反驳;好在我们谁的心里都明白,对付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任你如何去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不过,在挖掘机跟前监督捡矸石,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离得远了看不清;离得近了,挖斗不停地在头上和脚前时而升起、时而降下,谁也不敢保证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依旧还是在坑道里做着我们该做的事情。采矿负责人说了半天,最终也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结果,最后他只是又气又无可奈何地甩出一句:“还真莫见过这么一块一块捡石头的呢!”下来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过了两天,可能是采矿负责人请示了他的老板抑或老板主动向他授意。只见他一反常态,和颜悦色又不无诚意地对我说:“干你们这一行也不容易,看你们开那点儿工资也太少了;我的老板有意给你们开一份工资,你们四个谁都有份。钱也不算多,可怎么比你们公司开的要多点儿。咱们一块打交道,也是有缘分,老板就是想表示一下,莫别的意思。”傻子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谢谢你老板的好意。麻烦你转告你老板,就说心意领了;但是,工资绝对不能要。无功不受禄,俺们一个打工的,没有什么本事,不但什么忙也帮不了你老板,而且干的又是光挑毛病的活儿,你们能理解俺们就知足了,什么工资的话就不要提了。再说俺们又不是给你的老板打工,干嘛要她的工资,把俺们看成什么人了?”我理所当然而又不失礼貌地回绝了他的“好意”。可是,他却不以为然,好像是认为我在说客套话似的抑或根本就没在意我在说什么。接下来他似乎很自信又很轻松地继续着他的话题。“其实对你们来说也莫啥,你们天天该怎么来还怎么来这儿,省的来也不来传到公司里去怕对你们有影响。你们天天来转转晃一下,说起来来了就行了;下来找个地方想喝酒就喝酒、想干嘛就干嘛去。到时候不管是吃了喝了还是干了别的什么的,记上账就行了,下来有人掏钱,你们就别管了。反正你们公司里也莫人来这儿。你们不在这儿的时候,俺们该怎么装矿还怎么装,看见石头也得检出去,肯定不给你们脸上擦黑,你们就放心吧。再说你们也都上了几岁年纪了,省得天天在坑道里蹲着,哪儿可忒不安全,常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要是按刚才说的去办,对谁都好,你看这粘不?”说到这儿,采矿负责人似乎有意停顿了一下。他见我一直不作声,便接着说:“钱的事不是问题,要是嫌少,我回去的时候给老板说一下,再给加点,这点儿面子我觉得她会给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摊牌了。结果自然还是我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采矿负责人一脸茫然,他疑惑不解地连连摇头叹息:“唉,真莫见过现在还有这号人,给钱都不要,那出来打工为个啥?”不过后来时间一长,双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他却由衷的感叹道:“你们也太正直了,唉,现在像你们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我走过的地方也不算少,在别处还真莫见过。”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我曾耳闻目睹过那些因贪婪而给集体造成严重损失的人和事。有的单位和部门的当权者,一旦被行贿者所贿赂,最终的结果无不是以不知高出其受贿额多少倍的不应有的集体利益损失为代价,而“回报”行贿者的。最可悲的是,如此惨重的代价,却是在一切都顺理成章或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而装进行贿者的“腰包”里去的;甚至那些不知情的人们还认为,事情本应该就是这样的。不过,被行贿者“俘虏”的当权者和别的不管什么人,自从他接受贿赂的那一刻起,他在行贿者面前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就不得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了。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堂而皇之的样子,以掩盖其内心的不安和龌龊,因而他又是可怜的。所以说,但凡有点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或者懂点人格修养和人生哲理的人,是绝不会为眼前的一己之私利,而最终干出这等害公又害己的勾当的。
随着开采量和运输量的增加,考虑到山下乡村道路狭窄和白天有行人及车辆的影响。向公司运送矿石的十几辆大卡车,只好选择在夜间装运。每天的傍晚,正值“夕阳无限好”的时候,我们一行四人,便从山脚下居住在沟口处的小院里出发,迎着西山顶上那轮又红又大的夕阳和夕阳照射出的晚霞,一路西上赶到苦木沟半山腰间采矿的地方。一阵炮声过后,我们的工作便从此开始。在弥漫着硝烟气味的坑道里,看不到夕阳是否落山,看不到天边还有没有五彩缤纷的晚霞。这里看到的只有身边的峭壁,还有脚下刚刚爆破崩碎的铺满整条坑道的矿石(当然里边混杂着一定数量的矸石)。踩在还散发着火药味儿的矿石上,偶尔还会发现有未炸响的瞎跑,那出露在外边的一红一蓝的雷管脚线,格外扎眼。在坑道里,时时刻刻都会让人提心吊胆:脚下那还安装着雷管的未炸响的瞎跑,会不会爆炸呢?身边这岩石和沙土混杂的峭壁,会不会坍塌下来呢?前几天,三名炮工在坑道里打眼时,靠山体内侧的那面峭壁,曾发生过局部的坍塌事故,这三名炮工侥幸逃过一劫。还有一天的中午,山下村里的几个人,在现场没人的时候,好奇的跑到坑道里去观看,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靠山体内侧的峭壁上塌下一块石头,不幸击中一人的头部,那人当场毙命。身临其境,每当想到这些,就竭力克制着自己不再往下想、也不敢再往下想了。
夜幕降临后,越来越黑暗的坑道里,经常看到有两束光亮。一束是挖掘机前照灯照出的光亮,它照在前方坑道里的矿石上,给挖斗不停地扒矿照明;另一束是一个人手里拿着的矿灯照出的光亮。这个人就站在挖斗的前面,用矿灯照着挖斗扒矿的地方,监督着挖掘机在扒矿的同时,把随时暴露出来的矸石,让挖斗单独一块一块地捡起来,然后甩到坑道外侧的岸上去。这个人还不时地弯下腰去,用随手拿着的一块小磁铁,不停地在挖斗扒矿的矿石堆上试来试去;因为在黑夜里有些矸石与矿石很难分辨,只好用这种办法来鉴别。这个身材胖胖的人,不一会儿,就显得疲惫了,但他依旧不停地重复着上述动作,这个只身站在坑道里的人就是张工。和张工打交道已经有些时日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有着急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沉稳和认真的人。即使在险象环生的坑道里,他仍然不慌不忙,四平八稳地做着他该做的事情,从不遗漏任何细节,那神态和认真的劲儿,似乎和他平时没有什么不同。有一天的夜里,他正在坑道里监督着挖掘机往外捡矸石,这时一阵寒冷的山风吹过,靠山体内侧的那面峭壁上,突然落下一块酸枣般大小的小石块,正好砸在他的头上。只见他稍微一怔,瞬即用手捂住头,下意识地向上看了一眼身边那面高高的峭壁,然后低下头来,一声也没吭,紧接着又继续做起他要做的事情来。事后,过了几天才知道,他头上砸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包。就这样他一直带着伤坚守在坑道里,明知坑道里险情难料,也完全有理由休养几天;可他自始至终只要坑道里有装矿任务,就一次也没有离开过。他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不让别的同事到坑道里去或少到坑道里去。但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用实际行动这样去做的。不知情的人,谁会想到这是一个有着渊博知识的地质专家的心胸和所为啊!
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站在坑道里的我,面对眼前的场景:灯光所照之处,只见头顶上的“一线天”纷纷飘落着密密麻麻的雪花;脚下踩着的矿脉上还有几个未引爆的炮眼,炮眼里引出的雷管脚线零乱地散落一地;阵阵寒风夹杂着雪花和挖掘机装矿时掀起的尘沙,不时地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又痛又冷;这时只能眯缝着眼监督着挖掘机在装矿的同时向外捡矸石。此情此景,心中不由地萌生出一种难于言喻的凄楚之感。我不由地扪心自问,何以至此呢?其实没有任何人具体要求我这样做,那为什么自己把自己弄到这般田地呢?为了少往公司拉几块矸石,置于冒这样的风险吗?同时让同事们也跟着冒险,万一要是有个不测,又如何交代呢?我心里翻来覆去陷入左右为难之中。要是不进入坑道,那自然是安全了;可是,在漆黑的夜晚,在矿石和矸石混合在一起的坑道里,如果失去现场监督,任由采矿方自行装矿,那意味着什么?对公司选厂又意味着什么?如此这般,“吃着俸禄不担惊,”把明知矿石中混着不少的矸石一并装运到公司去而无动于衷?那样的话,职业操守何在?又如何取信于人?即便是公司没人说什么,自己又于心何安呢?思来想去,最后我觉得只要有一点办法,还是要坚持下去。我之所这样想,自然有不负上司在关键时刻对我的信任、也不乏有回报知遇之恩的因素在内,但更多的是良心的使然。然而最终之所以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并一直付诸于实际行动,则是源于同事们自始至终无一人退缩的结果。明知坑道里有危险,却依旧拖着疲倦的身子,默默无闻地坚守在那里,厮守着心灵深处的道德底线。这大概只有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有着良好的职业操守、注重自身名誉和道义并甘于患难与共的同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做,尽管谁都无一句怨言,但我心里明白,每个人都在捏着一把汗,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只有小王带着感慨的语气问过一句:“张矿,咱们这种干法,公司那边知道呗?”“应该知道吧。”我随口而出。但心里在想,看看送过去的矿石质量如何,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这天夜里,雪不停地下着,凛冽的山风不住地吹着。在后半夜,地上已经渐渐地结了一层冰。见这样的路况,采矿方马上收工。拉矿的卡车这时无论装上矿的还是没有装上的,都迫不及待地在车轱辘上安装上防滑链,然后迅速向山下开去,唯恐地上的冰越冻越结实而无法下山。我们乘坐着越野车在下山的一处拐弯路段,车子曾一瞬间在结冰的路面上打滑行驶,情况十分危急,幸亏最后总算停了下来。我们只好下车步行下山。但是,为了不把车子冻坏和不影响明天的出车任务,小王就是在这样的路况下,硬是冒着危险把车子开下山去。
一辆较旧的拉矿卡车,在公司附近的一段上坡路上,因雪天路滑,无论如何也开不上去了,被迫停在那里。消息传来,已过子夜时分,正值人们熟睡之际。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公司的小秦和李俊校二位部长打电话求助。他二人从梦中醒来,得知情况后,谁都二话没说,立即穿上大衣,迅速赶到料场招呼了一辆铲车,随后带上钢丝绳马不停蹄地赶赴现场。经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终于把那辆拉矿的卡车拖上坡去。事后,卡车司机非常感动,包括采矿负责人也为之动容地说:“你们公司粘,大摊儿就是大摊儿,到了事儿上按牌码。这事儿要是搁在别处,才莫人管哩。正规的摊儿就是不一样,也赶上遇上好人了。”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一天的下午,坑道里靠山体内侧的那面峭壁,顷刻间坍塌下来。我们闻讯赶到时,只见那条狭长又深邃的坑道,已经全部被坍塌下来的石块所掩埋,覆盖在上面的最大的石块有碾盘那么大。幸亏当时坑道里没人,不然有多少人也跑不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我们几个人只是呆呆地凝视着,半天谁都不说一句话。昨天我们还在这坑道里,此时此地每个人是怎样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采矿方才把覆盖在坑道上面的土石方清理出去。监督装矿的工作又开始了。我们一行四人,又重复着每天迎着夕阳上山和披着星月下山的日子。 如此日复一日,不知不觉当中,迎来了阴雨连绵的初夏时节。随着坑道不断地向深部开采,两侧的峭壁越来越高了,靠山体内侧的那面峭壁,现在已经高达40多米。经过雨水的不断渗透,坍塌的危险再次笼罩着每一个在场人员的心头。为了统筹兼顾安全和矿石质量问题,我们只好采取单人轮流当值的办法,继续风雨无阻地坚守在坑道里。一天的傍晚,当我们照常上山赶到现场时,突然发现坑道的中部塌陷出一个黑洞洞的洞口。原来下边是一条过去开采过的坑道,新旧坑道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矿体相隔。站在这黑洞洞的洞口旁边,我久久地俯视着这看不到底的黑洞,脑海里禁不住浮现出昨夜我曾在这里站了很久很久的情形。此刻,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骤然涌上心头。恰在这时,忽然感到头顶上的“一线天”上空,迅速掠过几只飞禽的黑影;接下来便听到高空传来几声凄厉的惊叫,那声音久久地在耳畔回荡,过了许久才渐渐地远去。
苦木沟历时半年之久的采矿,终因资源接近尾声和险情的加剧而宣告结束。半年多来,对装运到公司去的矿石质量,只能说,我们始终如一地尽了应尽的努力。另外,通过对装运矿石的车辆采取逐车登记、每趟签发发货单和跟踪监督等一系列措施;最终经与公司核对,从采矿点发出的矿石,均一车不差地如数发到公司,并且中途从未发现其他异常现象。
苦木沟又恢复了它原本的寂静。有感于苦木沟这段刚刚结束的不寻常的经历,我随即写下开篇那首《七律·苦木沟》,以志纪念。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转眼离开苦木沟已经六个年头了,我也由“知天命”而到了“耳顺”之年。但是,无论时光和环境如何变化,在苦木沟的那段经历,却时常不知不觉地浮现在眼前。我难忘那道考验心灵、磨练意志的山沟,更流连山脚下沟口处的那个久居过的小院,那首《壑院秋色》一直陪伴在我的心中。“环山庭院静,窗外草木青;朝有杨枝鸣鹊,夜有柿稍弯月。览沟壑丛翠鸟语绕,听蟋歌秋晚清音伴;庭台独馨处,不觉月色满院。”每每默诵至此,便勾起我对那片幽静的环境无限的憧憬。然而对我印象最深或者说已经铭刻在心中的,莫过于在坑道里同事们那紧绷着的脸庞和疲倦的身影了。那是一种多么真挚和纯洁的工友之情啊!那是一段多么值得珍惜的岁月啊!
2017年3月25日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9043 准媳妇
- 浏览:7881 祖孙情
- 浏览:7385 战将观后感(一)旋风司
- 浏览:6202 《农民工》接龙
- 浏览:5723 “句町”读音辨析
- 浏览:5590 好事近
- 浏览:5114 效率才是第一生产力
- 浏览:4839 生活中的辩证法(随笔)
- 浏览:4685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观后感
- 浏览:3821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