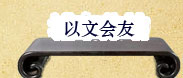生产队趣事 
退休之后,突然清闲下来。按说忙活了大半辈子了,儿女也成家立业了,闲下来好啊,没有事情做好啊,可是偏偏身子清闲了,脑子却不清闲,翻江倒海地想事,而且是近期的事想不起,越是久远的事越能记得起,想得清楚。唉,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怀旧情结?
回到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那时麦收和秋收秋种学校里要放假的,让学生回到所在的生产队劳动,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那个时代嘛,科技不发达,农业机械匮乏,人力是主要的生产力。十三岁那年秋假,生产队队长安排我和一名机手(会操作潍坊产的195柴油动力机)夜间去浇灌已经播好麦种的麦地。吃完晚饭,我和这名机手(男性、约四十岁左右)去村北麦地接了班,待白天劳动的二人离开后,这名机手从我手中接过铁锨,开通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副水渠,并用开通时挖掘的土把南北走向的主水渠堵死,这样水就不会南流、转向西流了。然后又把副水渠连接的麦田畦一连开通了八个出水口。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说话,我也没有问。待他做完这些后,左手一手扶着锨抦,抬起右手指着主水渠堵口的南边说:“你就在那睡觉就行了,放心睡到天明,今夜抽的水只能灌溉这八个畦子。我在北面看机器。放心睡,地里干得很,不会起人(因潮湿侵害人的关节)的”
我很感激他,觉得他是一名合格、负责任的公社社员。因为刚才他所做的一切,应该在我的劳动范围内,况且还能一觉睡到天明呢。
毕竟是孩子,毕竟是第一次晚上劳动,毕竟是第一次在野外露宿,天刚一放明,我一个激灵就醒了。醒后神经质地查看灌溉情况,觉得八个麦畦肯定已经灌溉完,紧接着要改水渠道了。但是令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南北主水渠的水刚刚流到副水渠的开口处,而且没有流水,只有水痕。在我立即想到水手的同时,也感到了水井旁的195柴油机不正常的轰鸣声。我一边呼喊着机手的名字,一边跑向机井处,发现柴油机连接离心抽水泵的皮带已经脱落,没有了负载的机器发疯似的空转,而机手却不知在哪里。开始我不敢接近195柴油机,又怕机器飞转损坏,最后大着胆子将柴油机息了火。在我守着这一套灌溉设备一筹莫展的时候,隐隐约约发现从西边走来了一个人,待看清是机手的时候,心里是豁然开朗,原来机手是回家睡觉了。
简单交流后,机手重新发动机器,离心水泵的水又开始流向了主水渠。这时机手说:“如果队长问什么没有浇着地,你就说机器坏了。如果队长问机器怎么坏的,你就说,我小,不懂,反正是坏了。”
好在队长也没有问,但是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地印象。
过了春节,转眼到了麦收,学校又放假了。快要过年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坚决地辞职了,大队干部年前年后在我们的生产小队队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在正月底落实好新的队长。是我家对门、按街坊辈我喊叔的人,兄弟三人,排行第三,五十多岁,我喊他三叔。三叔死活不干,说自己没有本事,领导不了社员。大队长说:
“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就是轮换着干,也该是你了,你看看你们队谁没有干过队长?”
大队长说的是实情,准确地说结了婚的男性数到六十岁,几乎都担任过生产队长。三叔如其说是走马上任了,还不如说是被逼上梁山了。
俗话说三秋不如一麦忙,三秋指的是秋收秋种,一麦指的是麦收。一麦忙、忙的是一个抢字。因为这个季节天气变幻无常,更是下冰雹的季节。如果不抢收,万一一场冰雹下来,或者是遇到连阴天,半年的收入就泡汤了。民以食为天嘛,口粮保不住,那要出大滥子了。
生产队的场院(晾晒、存放庄稼的地方)里只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负责人(俗称场院头)和六个十几岁的学生娃在晾晒小麦。约十点钟,三叔从坡里回到了场院。场院头手里拿着一杆叉立即迎了上去:
“队长,这样安排不行,孩子们还小,没有力气,干不动活,你总的安排几个大人吧。”
“坡里也急,首先咱得先收割回来吧,真安排不出人来。”三叔一脸的焦急,嘴唇上也暴了皮。
“不行,你去找找她们,不能上坡里割麦,在场院里帮帮也行。”
一说她们,三叔明白说的是谁,是四个娘们;兰花、丽萍、秀美、美珍,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带头的是兰花。那个时代,粮食按人口分配,随收随分。出工记分,到年底累计工分、按工分多少分红,也就是分钱。可是往往到了年底,生产队除了上交费用,以及生产队的日常费用和生产投资,分到社员手里的钱寥寥无几,甚至出现负数,不能分红。兰花看到了这一点,她觉得整年出工出力的,到年底分几块钱、十几块钱,不当油不当盐的,还不如不去出工呢,反正是吃的东西按人口分,所以就以有病为由,请了常年病假。之后丽萍、秀美、美珍效仿她也请了常年病假。之后四个人经常在兰花假的大门口聚坐、说笑。全队社员们都知道她们是装病,可是人家就说自己病了嘛,官不差病人嘛。
三叔正要走,场院头指着我说:“让他和你一起去吧。”然后向三叔使了个眼色,那眼色怪怪的,但三叔领会。这样我和三叔去了兰花家,老远就看到四个人在大门口张牙舞爪地、笑声也传了过来。走到跟前,三叔对着那个白胖、满脸红光、正在哈哈大笑的兰花说:“兰花大妹子,麦收了,场院里缺人手,你们…”
三叔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兰花后仰在门框上,伸长着脖子,张着口,喘气一顿一顿地、喘不上来,两眼向上呲喽着,眼眶里几乎全是白眼球,嘴里的涎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这这这,这…”三叔嘴里说着,落荒而逃。我,紧随其后。
麦收时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在坡里割麦,一部分人将割倒的麦子拉回场院,一部分人在场院里晾晒,到了晚上再组织一部分人将晾晒干的小麦用脱粒机进行脱粒。
晚饭后,听到三叔敲钟,社员们就到钟下问:“带着碗吗?”
如果三叔说带着,场院里就会聚集满满一场院人来脱粒,等到脱粒机运转时,围在脱粒机旁劳作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不是在场院边,就是在麦秸垛后或黑暗处,待到中途(一般干到晚上十一点结束)、大约晚上九点加餐(一人一碗绿豆汤或一碗面条)时,场院里呼啦啦就布满了人。如果三叔说今天晚上不带碗了,就有很少人到场院里去了,甚至是因为人手不够,不能启动脱粒机。
尽管集体干活时、是出工不出力,甚至是连工也不出,但是如果谁家打墙盖屋、婚娶、丧葬需要帮忙,大家都是尽心尽力地帮忙。有的管顿饭,有的不管饭,管饭的饭菜也及其简单。管也好,不管也罢,大家仍然是全力以赴。
今天,社员这个词没有了,人人变成了公民,人们拥有了高度的自主权,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兰花她们知道自己是公民后,有了觉悟,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拼命地劳作,成了全村最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有很多时候,我守着满餐桌的鸡鸭鱼肉、喝着个小酒、在想,为什么现在一个人跌倒在大街上没有人敢去扶呢?为什么有人主动撞到车上,不惜把自己撞伤呢?为什么一个清纯的女孩自己去制造自己乱伦、乱性交的绯闻呢?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社会像一艘在波涛汹涌中航行的大船,左右摇晃,弄不好极易偏离航线甚至倾覆。要想让它行稳致远,最好也像火车一样,给它加上牢固、不可逾越的铁轨。这个铁轨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期待它的出现。
作者简介:陶兴国,男,笔名晨雨,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人。工作之余喜欢阅读和撰写文字,用敲打的方式记录生活的美好和岁月的沧桑。邮箱pdchenyu@163.com电话13280830098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9044 准媳妇
- 浏览:7883 祖孙情
- 浏览:7386 战将观后感(一)旋风司
- 浏览:6204 《农民工》接龙
- 浏览:5724 “句町”读音辨析
- 浏览:5592 好事近
- 浏览:5115 效率才是第一生产力
- 浏览:4841 生活中的辩证法(随笔)
- 浏览:4686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观后感
- 浏览:3823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