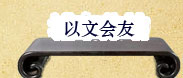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可以说对多数家庭来说是经济短缺期。缺吃少穿,生活紧张是一般家庭的主要写照。当时我全家只有父亲一人在邢台矿务局工作,我们姐弟四人都在上学,经济自然更加紧张。平时母亲主要承担起教养我们姐弟和照顾我外祖父的重任。外祖父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据说两个舅舅在战火年代连续夭折。外祖父姓吴,也是文化人,身高接近1米八,很斯文。他早年曾在著名的北京六国饭店等处工作,北平解放时有朋友征询和劝说外祖父以民主人士身份留在北京,时恰逢继外祖母病重,他就托辞回到祖籍邢台沙河县曹庄村照料外祖母,我这个外祖母是他的继妻,自此未再回京。后来土地改革时候,因外祖父家里也是当地大户【外祖父姐弟八人,他行八。家有土地和马车等许多家业】而被斗争。外祖父晚年体弱多病,全赖母亲照料。母亲就只好一边在生产队劳动,一边抽空去照顾我外祖父。再后来因为生产队农活很忙,夏秋收割,春冬翻地等,轻易不休息。为了方便照顾外祖父,母亲就只好忍痛把当时还未成年的姐姐留在曹庄上学和照顾外祖父。
那时候粮食奇缺,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分给社员都是定量供给制。生产队根据每人平时劳动能力的大小评估出每个人每日劳动的分值进行积分。在夏秋季收完庄稼后,生产队先交足公粮,再按照劳动者的工分积分给社员折算分得粮食或粮票等。劳动者多的家庭自然就分得粮食多,当时我很羡慕人家。我家只有母亲一人劳动,分得粮食甚少,基本吃不多久就空仓了。母亲就常常借着粮食吃。我父亲在外工作,母亲独自在家留守,这样的家庭在农村叫“一头沉”,意思是夫妻一人在农村,一人在外上班挣钱。当时这样的家庭在生产队最受欺负和残酷剥削。平时分配农活时,给这样家庭难干的活儿。到分粮食的时候,父亲就得用钱交到队里换粮食,给会计很多钱,换取不足全家人半年的口粮。另外当时的生产队长很孬,除了使着劲给这些“一头沉”家庭要钱,还故意让“一头沉”家庭排队到最后分粮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一头沉”们当年可怜巴巴地在粮场外边等着分粮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直想揍那队长。
为了换取更多的生产队的工分,减轻父母经济负担,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到整个中学时期都是边上学,边于节假日参加生产队劳动。我是学生,根据我的劳动能力被评得7.5分值,这在当时的学生劳动群体中属于高分了,成年的劳动力一般是8-10分【一般妇女是8-9分】。农忙时,我在生产队收割麦子,掰玉米,打麦场,赶排子车拉农肥,装沙等。因为我和队长儿子经常一起玩,队长安排农活时也照顾我。农闲时我就给自家喂养的猪或生产队的牲畜割草,或者周六日休息时我常背着筐子沿路捡牲畜粪便交给生产队作农肥,借以换得工分,以便日后好多分得粮食。深秋季节,我凌晨去树林扫树叶,交给生产队沤粪当农肥;中午沿着公路拾粪,困了就睡路边。有一次拣粪差点丢命。我跟追着一辆往端庄火车站送沙子的马车捡粪便,途中看到在火车站南边东西过路上的双轨之间有两大堆牛粪。见当时周围没有别人争抢,只我自己,我很高兴,顺便向南望了望,见火车尚远。当时没向北看,就匆匆冲过去。等捡完牛粪,准备离开时抬头一看,南边火车已近在眼前。再向北望去,一列火车也由北向南疾驶而来。南北的两列火车相向,把我夹在中间。我顾不得多想,背着筐子纵身一跃就飞出去两米远。只听得我身后的火车呼啸而过,一阵风差点把我拽倒。此时旁边的一位铁道护路工看看表说只差几秒钟我就会丧命,他拦住并扣下我,让家长来领。我哭着求情,一个在车站工作的同村人恰好路过也帮助我求情,我才得以被放回。
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喂养了两头小猪和圈养数只母鸡。我们不时去野外田间给这些张嘴等吃的动物们搜寻食物。但我贪玩,懒惰。弟弟勤快、实在。打猪草时我经常偷懒。一次我和弟弟一同去打猪草。到了地里,我先是玩,想等到最后再割草。弟弟一直割草,不停歇,割了很多草。我却因贪玩,收割的青草甚少。眼看日照夕阳,该收工回家了,我仓促找到一颗硕大的掃箸苗,放在筐子底部做支撑,筐子差不多就显得充满了。我再匆匆忙忙割了少许青草在上面遮掩住,然后带着弟弟回家。到了村里,我不直接回家,而是直奔我家的猪圈,先把筐子里的草喂了猪。之后让弟弟把他割的猪草带回家。母亲看见我筐子空着,就问我割的草呢,我回答说先喂给猪吃了,母亲到猪圈一看猪食池子旁果真剩有少量青草根儿,也没再多说。我总算侥幸躲过这一关,否则必挨揍。
七十年代,一日三餐吃的主食基本是粗粮加野菜。我家分得的粮食又很少,吃不多久就没了。除了重大节日时偶尔外出借点细粮,母亲就常领着我们想法找吃的,或者去田野找野菜,或沿着铁道两边挡风林采摘树叶,然后回家用开水汆熟,再用盐调和着吃。或稍加麸子面等做成菜团吃。那时候采摘树叶也得秘密。田间的大部分树枝树叶都被采光了,许多人便把目标集中到铁路两侧的挡风林,铁道工人抓紧巡逻看护这些树木,发现采摘者就驱逐或抓住,我们只好东躲西藏、小心翼翼地采树叶。
后来的几年里生产队分发山药比较多,这种食物吃多了“烧心”【胃难受】。七十年代末期,队里在农田垄沟等到处大片大片地种高粱,我经常吃高粱米、高粱面类食物吃得大便不通,一位邻居大婶常不嫌脏臭地帮助疏通,现今回想起来非常感谢。 至于肉蛋之类副食几乎没有。家里圈养了三只母鸡,母亲好好饲养它们,只想让母鸡多下几个鸡蛋给我们吃。喂养的小猪长半大时就早点卖给公社屠宰站以换取些许零花钱。一年里只有春节、中秋等这些重大节日,队里才舍得屠宰猪分给社员每人几两猪肉,我们才能解馋闻到肉香。所以我们经常盼着过节。
无论分粮食还是猪肉等,队长和会计等几家总是分得多。村里的几个生产队长还经常互相打借条说是借着对方生产队的粮食种子,来年再还。其实后来我才得知,那是应付外边群众或组织的一种手法,借条上写的粮食都被这些人弄回自家吃了,可笑我当时不懂种子也能吃。我经常在队长家和他儿子玩,他家里只有队长一人是主要劳动力,但他老婆经常给几个孩子做鸡蛋煎饼和馒头疙瘩汤等吃。而且他家里总是有吃不完的麦子白面。
记得当年公社在沙河老县城南街设有一个屠宰站,定期屠宰猪牛等出售给村民,一斤生肉4-5毛钱。一对父子在那里卖肉,父亲70岁左右,儿子30多岁吧。每当我父亲发工资,母亲就常常带着我去公社屠宰站买肉以改善生活。和母亲每次去买肉,我们总是看人脸色,给人家说尽好话,想得到照顾多买点肥肉。因为那年代家里都缺少食物油,炒菜不香,只想买点肥肉回来用铁锅熬制脂肪油,炒菜用【那年代卖肉和供销社卖百货的人可吃香了】。姐姐在外祖父家住久了,母亲难免想念女儿。母亲惦记在外祖父家的我姐姐,于是有一次就多买了些猪肉,让我送去给姐姐吃。到外祖父家,外祖父把猪肉炖熟后先尽着姐姐吃,他和我在旁边看,我当时羡慕死了。我回来后,哭鼻子说再也不去送肉了。
有时候,我早晨上学急,没吃饭。母亲就会在半晌去学校给我送烧饼,那时候烧饼也是奢侈品,我舍不得自己独吃,掰一半给母亲,她不吃,只看着我吃,现在我脑海中还不时浮现出当时母亲慈祥的表情,很感动。
曾记得某年我休假住到父亲单位。父亲曾主管食堂【那时候这是美差呢】,我去了可以跟着父亲一起在食堂吃饱吃好,这是我最解馋的时候。后来父亲不管食堂了。一次,父亲给我5毛钱让我去食堂买饭。食堂有10个左右的售饭口,分类出卖米粥,馒头,玉米饼子,咸菜,肉类蛋类等各种饭菜,很丰富,整个食堂大厅飘着香味,馋得我垂涎三尺。大家都在排队打饭。我突然注意到卖咸菜和玉米饼子的窗口排队人特多,卖肉和馒头烙饼之类的那窗口排队的人很稀少。我奇怪地想,肉好吃,咋这么多人不去买肉,都排队买咸菜呢?我不愿意排队等候,于是就买了一份烧肉和几个馒头,很便宜的,一毛五就给了满满的一大勺子红肉。等我回到父亲住处,父亲二话不说就顺手打我一耳光,大声地责问"就你知道肉香?”,父亲嫌我浪费。当时一斤生肉才5毛钱,一毛五给一大勺子熟肉。八元钱就是一个大男人一个月最奢侈的生活费。
物资短缺的年代,穿衣服都是用买的洋布或家里老人纺织的棉布粗布做衣服。买布通常需要凭布票。每人一年发的布票很少,成年人和孩子得到的布票尺数不同,反正全加起来也买不足俩大人穿衣所需的几米布。于是,我们各家都是互相借着用,等来年发了布票再还给人家。
有时候,母亲照顾外祖父就在曹庄小住一段时间。我就转学在曹庄读复式班。几个年纪同屋上课,老师分开时间讲授,没有统一课本。刚上课,老师先让低年级书法临帖,或默写默读课文,倡导“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然后开讲书理,熟悉课文后再逐渐写作。针对高年级,则以自学为主,答疑辅导。三年级先作业,四年级看语文,五年级听数学【那时候没有六年级】,之后再换讲,别有趣味。当时母亲为了照顾外祖父,不定期在沙河城和曹庄之间往返迁居,我就随之来回转学。当时也没有统编教材和统一进度,转到各校主要看人家哪个年级学的内容和我接近就随机插班入读,导致我在各处所读年级不一。所以我各个年龄的同学都有,别人很奇怪。
在物资短缺的年代,物价特别低,但绝对是物美价廉、货真价实,基本没听说伪劣假冒。县委书记乘坐破旧的吉普车,县委县政府也就共用1-2辆,局长们都步行上班,鲜有骑自行车上班的。自行车在当时也属奢侈品行列,好点的有飞鸽牌、永久牌等,每辆约值200--300元多点,即使如此很紧俏。很多家庭都需要积攒几年的资金加上一张特种商品购物票,才能想法托门路购得一辆。我家有一辆九成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和一辆别的牌子的新车,我就是用这辆飞鸽牌学会骑车的。 据说当年的白酒全是纯粮酿制,基本多为玻璃瓶装,很简易朴实,几角钱或一元多一瓶。当时屠宰站屠宰猪牛羊等剩余的肠肝肚之类下料,因为不肥,卖不出去,就以一毛多钱的很低价格卖给喜欢喝酒的人们当做下酒菜。至于几分钱一盒的香烟,比如岗南、大刀、大前门、黄金叶牌香烟等尽管很便宜,大多人还是买不起,多数人抽自种烟草和自制的原味旱烟,尼古丁含量很多。甚至还有不少人经常在次日早晨去昨晚演电影的场所,寻拾别人扔的烟头回来拆开重新卷成烟卷抽。我们这些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就想学抽烟。几个同学还常偷家长的烟卷带到学校抽,或把蓖麻叶、丝瓜叶等弄干再卷烟抽。我父亲不抽烟,同学们就给我烟抽,我这样渐渐学会了抽烟,抽得上了瘾,手指发黄。一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上级主管想把我们单位办成无烟单位,要求我们几个基层领导带头戒烟,喝了戒烟酒,我才戒了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