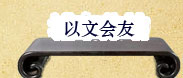回忆在一中(下乡支农篇) 
回忆在一中(下乡支农篇)
一
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就象电视剧《磋砣岁月》里的主题歌,“一支歌,一支奋进的歌…. 憧景与向往是那么的多…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汇成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终究从我们脚下趟过,如今我们已是年近古稀之人,但每当想起在一中和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学习生活的时光,仿乎又有了青春的活力….那段时光,总是那么令人难忘。
1964年,我从都匀附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都匀一中。那时的校长是王平,校支部书记是张润芝,教导部主任是李天敏。当时我分在初一(3)班,班主任是徐仁甫,教我们的语文,数学课老师是程远昭,政治课老师是花化龙,英语课老师是王子聘、黄世义,地理课老师陆永涛,音乐课老师是程敬秀、敖克诚,生物课老师是黄寅,体育课老师是王培。
经过了五十多年,好多的事都忘了,连很多老师、同学的名字也都记不起来,唯有读初一初二这两年,是我们真正的学到了知识的这段时间,最难忘。那时,踏入一中,就感到一切是那么的新鲜,上课不久,学校就组织全校师生下乡支农。
现在说下乡支农,可能初、高中的学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值得回忆的事很多,不能一一尽述,恰学生下乡支农,是我们那几届高、初的同学最难忘的事。现在我就把那时下乡支农的概况向校友们说说吧。
二
那时,每一学期都有下乡支农的活动,每到农忙,家住农村的学生可以请假回家去帮助抢收和耕种,城里的学生和不愿请假回家的学生,由学校组织到区乡公社的生产队去帮助抢收和耕种。
在下乡之前,老师们都为我们作了政治动员,说这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一次实践体验,大家要学习解放军、八路军,人民是水,我们是鱼,要向解放军一样,去到哪里就要同哪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做到军民如一家;早上起来,要帮助老百姓打扫卫生,挑水,割草,打柴,能做的尽量去做,不能做的也要争取去做,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去之前,老师还教我们打背包,学会之后还举行打背包比赛,我记得我当时手脚较笨,比赛得倒数第五名。
三
第一次下乡支农,是到凯口公社,我们班分在现在凯口乡北面的一个生产大队,这个生产大队住户很分散,大部分住户在凯口田坝,有一小队却住在高于田坝约300多米处的山坳,地名叫营盘,当时带领我们的老师是徐仁甫、花化龙、程远昭、王子聘。营盘的生活比较艰苦,那时的口号是“越是艰苦越向前”, 结果,由徐仁甫老师带我们班十五个年龄较大的同学上了营盘。
背上背包,徐老师带着我们向山上爬去,队伍弯弯曲曲呈之字形走在山冲小道,真象电影里的一支上山的游击队。到了营盘,生产队队长来迎接我们,他带领我们到生产队仓库的楼上,楼是木楼板,走起路来冬冬的响,这就是我们的住宿处,生产队的社员扛来稻草,同学们就自己去抱草来铺床,农村出生的同学会用稻草挽成一小捆作枕头,城里的同学用衣服叠好做枕头,然后,每个人把背包打开,铺上一床单,被子盖上,我们睡的床就成了。
徐老师也跟我们住在一起,为了我们的安全,他把他的床铺安排在门边,他向老百姓借来两条长櫈和木板,搭成个床,才铺上稻草、床单、铺盖,枕头也是用衣服叠好做成。
安定好住处,已接近中午,徐老师叫大家在楼下晒谷场集合开会,不断嘱咐说:“一会儿就有贫下中农社员来领你们上家,去到人家,要懂礼貌,年纪老的,要叫老爷爷老奶奶,主人家叫叔叔伯伯和大娘大妈,大哥大嫂小弟小妹要熟悉了解后再开口…. 要勤快,抢做家务事,要向解放军学习,做到每天吃饭要洗碗,农家院坝要打扫干净,厨房水缸要水满…”。
不一会,生产队长和贫胁主席带来十几个贫下中农社员,社员们是来领学生的,徐老师点到哪一个同学的名,那个同学就跟着一社员走了,不一会就分配完备,徐老师分在队长家。
据说,当时能接纳学生到家去同吃同住,是当时生活条件较好的人家,公社及大队经过排查才这样安排。恰我们到达的这个营盘生产队,比起其它小队,生活条件是最差的。
我到的这一家,是一六口之家,一对夫妇两个老人两个小孩,两老人已年近花甲,也还是公社社员的全劳力,所以,生活条件还算好的。可第一餐饭:菜是一大锅老莲花白的叶子用不到五钱的菜油烩成,饭是少量的包谷砂与红薯切碎拌蒸而成,真的是一颗米都不见,然而,我们这一代,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什么样再不好的饭菜都吃过,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填饱肚子就行。
吃完饭,生产队的牛角叫了(当时民族地区很少有钟,只有生产队长有一个马蹄钟,时间一到,队长用吹牛角的声音当信号),该出工了,我们随着社员又来到晒谷场上,听队长安排工作,队长分咐完备,我们就跟着社员上山了,主要的任务是收包谷。
你可不小看,生产队突然增加十五、六双手,包谷收起来很快,同学们争抢表现,社员们也暗自显能与学生比武,约十七八亩多的包谷地不到两小时,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从包谷地到生产队的晒谷场有约两里地,收好的包谷穗要抬运到晒谷场,社员们和我们大龄同学都用粪箩和米箩来挑抬,小龄同学用箩筐装成五六十斤一筐,绳索套筐,两人抬一筐也跟着挑运,我们来回挑抬了三趟,一下午收的包谷穗堆起来就象座小山。
同学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体劳动,很是兴奋,每个人都汗水淋淋,花门寥脸,却没人喊累,好象是在与社员们共同享受丰收的喜阅。
收工后,同学们又跟着自己的主人回家,回到家后,天已黑尽,点上煤油灯(那时,几乎所有乡村都没通电,照明全是煤油灯),女主人生火做饭,我帮女主人劈柴烧火,看到了整个做饭过程。
先是在大锅里加水,然后把约二斤的包谷砂放入锅内,煮至半熟,再用箜箕将半熟的包谷砂箜沥而出,再把约七八斤洗净的红薯切成如板栗大小的块状,与包谷砂搅拌;然后,重兴洗锅加水,放上木甑子,将用包谷砂拌好的生红薯从甑口用筷子慢慢赶下正冒热气的甑子里,盖上甑盖;这时,又用箜箕把老莲花白叶子切碎,放入甑底,加火蒸煮约半小时,饭菜就都熟了。
吃饭在火笼边(实际上是一间房屋,房屋中间用砖或石块镶嵌成四方形或六角形,可用炭、柴生火取暖,常作全家吃饭及待客的地方,俗称火笼边、火笼屋),火笼正中有一铁三角(现在不见了,铁三角是生铁铸成,上面是一圆圈,下面有三只斜立的脚),女主人从灶孔里用铁铲撮来火子(烧柴成的炭火),倒放在火笼,老爷子端来小锅,放在三角上,倒上约五钱菜油,炙辣,然后把从甑脚下舀来的老莲花白叶子菜倒入小锅,放上盐和少量的干辣椒面,搅拌均匀,菜就成了。
饭菜虽简单,但我们吃起来很香,当时,我们饭量都很大,一顿就可吃七八碗,(约合现在六七两米煮成的米饭那么多),为了不遭嫌弃,一般听到饭瓢刮甑底响,就不敢再添饭了,吃个大半饱,是经常的事。
饭后,回到住处,已近21点,同学们向老师汇报各自的情况,吃的饭菜几乎都一样,徐老师又给同学们作思想工作,有城里出生的同学说吃不惯,还被大多数同学批评为小资产思想行为,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住处就一盏加气马灯,老师在马灯下做笔记,做完笔记,老师又对我们作了革命传统的再教育,又讲了些革命故事,22点半熄灯,不一会,就有呼噜声响起,师生们共同进入梦乡。
第二天,天刚刚亮,约六点半钟,老师就喊起床,穿戴完备,就往我们的主人家跑,一进门女主人就用木盆舀来热水叫我们洗脸漱口,(洗脸帕和漱口缸均是我们自带,昨日洗脚时就放在主人家)洗完脸,我看水缸里没水了,就拿起扁担和水桶去挑水,女主人说:挑水地方很远,劝我不要去,等会他男人割草回来,他男人会去挑的。我说:我能挑,问明了挑水的路径,就去挑水去了,我心头暗想,我不仅要挑水,今早我就要向解放军一样,住哪家,就要把哪家的水缸挑满…不想出得门来,才知道水源居然在山脚,距寨子有一里多路,空桶是下坡,满水是上坡,全是石板简单拼铺的台阶小路,有一同学也去挑水,我们共同下山,来到水源处,一看,傻眼了,水源处是一山沟溪流,正遇大旱(据说,已二十多天没下雨了),水流很小,社员们用树皮作枧槽接住溪水,溪水象屙尿似的往下淌,下面有水桶接水,几乎三分多钟才接满一桶,已有十多对桶在那里排队,几乎近一个小时左右才轮到我们,当我们接好水抬走,后面又有十多对桶接着排,真是滴水贵如油啊!这时,我才想起昨晚我要跟老人倒洗脚水,老人不让倒,我洗完脚后,要倒水,主人家也不让倒是怎么回事—原来,用过的水,还要拿去喂牲口。
歇了两气,水才抬到家,女主人显得十分高兴,不断夸我:“还真能干,有出息!有出息!”我把水倒入水缸,还不到小半缸呢!从而为我原来的打算感到沮丧,显得尴尬,我欲再去挑,却又到了吃早饭时间。
牛角又叫了,该出工了,又象昨日一样,又去收包谷。路上,我们才看到,营盘这个地方实在太穷了,寨子周围田土虽多,可全是望天水田,今年大旱,大坝的田地颗粒无收,只有青山的山冲里包谷长势还行,可距寨子则有二三里地……
在那段时间,我们还看到这样的现象,包谷收到生产队队部,晒干了的包谷穗,专门安排人在剥籽,旁晚,等米下锅的社员,手里拿着口袋,排成长队在向生产队借粮,保管员一升一升的印,会计就计:XXX家借包谷X升。(你也许会奇怪,自己种的粮食还要去借,这成何体统?实际上是,当时是集体所有制,所有集体土地种的粮食均收入生产队,上交公粮后才拿来凭工分和人口分,当时叫分红,有时除交公粮后,分到社员手里的粮食,不够吃到半年,甚至只够二三个月!很多人家全靠自留地里种的红薯、荞麦、红米及山上野果野菜掺合,才熬到新粮出来)。可见,当时政策的偏左,人们为了生存,所付出的艰辛!
作息时间是早饭后(约8-9点)上工,中午吃少午(即中饭,约13-14点) 下午出工(约14-15点) 晚上收工(约18-19点) ,就这样,我们在营盘支农一周,包谷收完,就下山了。
四
山下田坝是稻谷多,包谷少的鱼米之乡,还有约三分之一的稻谷未收完,我们从山上下来,继续帮助抢收,(当时戏称是支援兄弟部队)全班同学及老师大聚会,各自互相交流支农情况和炫耀所取得的成绩,并还开了表张大会,政治老师花化龙还把我们大龄同学召集开会,(当时,我们班16岁以上的同学有十多个,年龄最大的同学叫罗时平,已18岁,都因读书起步晚而形成)鼓励我们争取进步,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
我们的到来,是掺合在原同学分在的社员家生活,下坝的生活水平比营盘的好多了,虽然也掺杂粮,但总算见到白米及瓜豆等蔬菜,相比之下,真乃天壤之别。到田坝劳动也轻松很多,男女同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情景随时可见,师生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忿充满田坝,同学们的外号:什么“八大碗”“ 孙麻子”“ 小书包” 就在那时产生;旁晚,收工回来在凯口河边洗脚洗手互相嬉戏打闹…. 晚上,师生们还开互为鼓励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那时那景,构成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共同进步动人而又激情的一幅幅图画。
五
约半月的支农活动结速了,有汽运公司的客车来接我们回城,其它年级的学生都是在生产队住地直接坐车回校,而我们年级的老师却别出心裁,带领我们穿越山洞后才坐车回城,这对于我们无异于象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一样新奇,结果,一次象探险,又象旅游的穿越山洞活动,让我们终身难忘。
原来,凯口公社的东南方有一大山洞,从洞的入口这头从中穿越,据当地人说,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到达另外的平浪公社RQL(现为保秘单位)地区,可以节约车程近20多公里。据说以前凯口人徒步赶场赴平塘县城,是最近的一条路。
恰我班同学王绍伟的家就住在这洞口的附近,不用响导就可找到。
绍伟同学带我们来到洞口,洞口在一半坡的山崖上,有之字形的小路向上盘徊,上到洞口,一看,洞口呈一象狮子张口样的斜横岩峡,伸延有近百多米长,百多米长的中间,有用麻条石砌成的石拱城门,两边的城墙也是麻条石垒成,城墙还设有瞭望台及垛口,延伸至两边岩峡的尽头,里面还残留有原始的灶台和破碎的陶瓷瓷片及砂锅碎片;老师们议论说,这里应该是古时少数民族部落居住的地方,或是土匪的巢穴,但都无定论,只好让人们去猜想。
越过拱形城门口,就进入山洞,由徐老师和王绍伟同学带路,花化龙和程远昭老师护队,王子聘老师押后,我们就开始钻山洞了。
山洞一直是下坡,好象比爬上洞口的盘徊山路还长,渐渐的眼前一片黑暗,两米距离不见身影,老师和班干拿着手电筒照路,路都是多年人行走后形成的,说是羊肠小道一点都不过分,同学们有的手拉手,有的牵着前者伸出的竹竿前行,尤其是程远昭、花化龙两老师,不停的喊:“顺着路走,不要离路”“ 慢点,小心!小心!..这里有个石坎….”
下到洞底,却是平坦的大厅,脚下全是细细的泥沙和岩灰,踩上去就象厚厚的冰封雪地被踩裂陷的那种感觉,觉得心头一下子酥溜溜的;往前看,大厅一片黑暗,宽看不到边,高看不到顶,老师和班干的手电筒象萤火虫样在黑暗中闪烁;回首看洞口,洞口就象一全封闭的大仓库开了一个椭圆形如晒垫大的一个天窗,天窗的阳光象雨后斜阳把洞口顶照亮,洞口还有没下来师生在亮处,人头晃动及身影形象就象南极的小企鹅一样;亮光下就是黑暗浓浓的洞穴大厅,顿感神秘无比,五十多个同学和老师都只顾四处观看,惊讶得不敢大声说话…瘆人幽深的忿围使胆小人感到心悸,然而,这是集体行动,形成老师和同学们的互为鼓励信任的智慧胆略,没有人有恐惧感。
空旷的洞穴大厅究竞有多大?我们班的张万春同学是足球运动的守门员,去到哪里都随身带个足球,在洞底一稍高的小平地,他把足球从网袋拿出,做出守门员发球的动作,一大脚就把足球踢向黑暗,意为球碰上岩壁,会有回弹的声音,然而,只听嘣的一声,足球在手电筒的光中一闪,就渺无音讯,连落地的声音都听不到!几个在他身边的同学和他自己,顿感神秘莫测,老师们规定不许离路过远,至今那足球落在何处,可能将会成为千古之迷。后来,我们常提起此洞,据当地人说,若是把整个凯口公社的人家都搬进去,这个洞都容得下!
老师和班干们不停地叫唤:“顺着路走,不要离路,不要掉队!”洞底路全是平坦的泥沙路,很好走,走到狭窄处(也有10-20米宽),手电光要亮得多,还可看到奇形怪状的石钟乳形成的石幔、石魔菇、石笋等,快走完第一个大厅,迎来最黑暗的一幕,路也不太好走,老师和班干把手电集中照亮,方安全通过。
真象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过了上段最黑的难走之路,稍拐一小弯,眼前一亮,从左边洞顶又出现一个天窗,把洞底照亮,不要手电照亮也可走,但这段路全是大小不等乱石堆就,站在乱石堆的高处向天窗口看,隐约还看到石砌的拱门和城墙,一条小道从陡峭的乱石坡吊伸到洞底底壁,很多同学都认为要从那里出去,但那小道遍布蛛网,几乎几十年无人走过,没有现代人留下的痕迹。中心的洞道显示出路还在前方,这段路起伏叠宕,崎岖难行,约近百米不用照明,过了这近百米不用照明的路道,又迎来了一片黑暗,中心洞道渐显宽畅,走不多远,又是一个洞穴大厅!大厅亦是细沙和岩灰形成的平坦砂坝,宽大而高旷,深幽亦不可测。
这第二个洞穴大厅,虽然幽幽深深,但路道十分平坦,好象是古时候的干枯河床,手电光可照看到两边的岩壁,岩壁上还留有先行者用粉笔打的方向标,写下:“向前走,就可到路口” 的标语,这是最长最黑暗的一段路,走过这段路,又碰上一有天窗的大厅,这大厅的天窗却在头顶上,是一个滴水大厅,中央形成一小石山,在这里可清楚看到洞顶有多高,同学和老师都住足仰看,四周悬吊的石钟乳如彩云追月,如乱云飞渡,如二龙戏珠…任人暇想。
经过近二小时的徒步穿越,洞穴还向前方延伸,突然又看到了一个天窗,洞穴豁然敞亮,在一岩壁上划画有方向标:“由此出洞” 。终于看到了出口,出口亦是陡峭的斜坡小道,有石砌的台阶,呈蛇形向洞口伸出,没有阶梯的路面坎坷,师生们互相搀扶照应的走着,走出洞口,顿觉阳光刺目,迎来新天地一片,终于到达距凯口(从山路上走)约30里的RQL地区。
客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上车,车行,于当天下午回到学校。
据说,这是黔南乃至贵州最大的洞,我们穿越的只是该洞一个小小的岔洞,乃冰山之一角,可见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那时的老师突发奇想,就敢带领我们五十多个学生探索、冒险,穿越山洞,没有任何现代安全设施,没有保险公司,也没有事先向家长说明,说走就走,现在有人敢吗?
六
从那以后,每当紧张的学习中,老师宣布X月X日要下乡支农,同学们就都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因为下乡支农生活虽艰苦,但与贫下中农社员生活,劳动,学习在一起,有同甘共苦的共产主义精神体现,使人感到其乐无穷。
后来,我们班先后到过栗木公社(现甘塘镇) 栗木大队 、杨柳街公社马坡大队、和马寨公社东冲大队支过农。因年代久远,其中很多有趣的情节都忘了,唯在马寨公社东冲大队的那次支农,其中的产生的事情,现在还深深印在脑海里…..
那次,我们班分配在东冲一生产大队,这个大队跟我们在凯口公社的那个大队人家分布性质几乎一样,(那时一个公社约有六至十二、三个大队,大队有三至七、八个小队),大多数人家住在东冲的大田大坝,偏偏有一个小队住在高于东冲田坝约三四百米的山峦顶上,这个小队还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斑竹园。
所不同的是,这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是挑选人员,而是点到谁的名谁就去,结果,我们班有十五名男女同学,由程远昭老师带队,奔赴斑竹园。
去时,是从东冲大队东北方向有一条山溪的山冲小路往上爬,近两三里多路不见人家,山路较崎岖,程老师年纪已大,爬山显得有些气急,大龄同学抢着要跟她背背包,她倔犟不让,当爬上半坡,大家都大汗细水的了,坐下来休息,罗时平同学才抢到她的背包帮她背,我找到一木棒给她作手杖,她还表扬我聪明。我们继续攀登,经过约一个半小时,终于到达斑竹园。
寨子叫斑竹园,山叫也斑竹园山,据当地老百姓说,这里是这方人家住得最高的一个寨子。
也是队长来接待,安排的住处是生产队队部,这次则是男同学住楼下,程老师和女同学住楼上,煤油灯变成了两盏,楼上一盏楼下一盏,楼梯是木板楼梯,楼亦是木楼板,走动起来冬冬的响,女同学打闹戏嘻楼下听得清清楚楚。楼下是水泥地,走动却没声音;跟历次下乡都一样,同样是稻草铺地铺,打开背包就是床。
程老师跑上跑下,不断交待注意事项,她象慈母样,还帮小龄同学铺床,嘴里还不断念叨:“要讲究卫生,床铺要理蹭抖,不许玩火,点灯由杨永德同学负责,其余的人不许有火柴”。( 那时,还没有火机)
随后,同学们又被分配到各家,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次的劳动是帮助社员们抢种抢收,抢收是收小麦收油菜籽,抢种是在水田栽秧和上山挖土种包谷。
那时,几乎没有化肥,种植水稻全用农家肥,农家肥还分两层次,一是撒秧青,所谓撒秧青,就是到山上去割嫩蕨类植物、青草和嫩树枝叶回来,撒在耕种的水田上面,几乎要铺满约十公分一层;二是撒完秧青之后,还要撒草粪,草粪由社员家里的猪圈牛圈里获取,社员家的草粪是记工分的,每一百斤记二至三分,还要自己抬到田里,方可获得。
草粪抬到田坝,隔不远放一挑,社员们和师生们就去撒草粪,谁要是怕脏怕臭就会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师生们挽起裤腿挿下水田就去撒草粪,手抓草粪满身臭,程老师还口中念叨:“要不怕脏,不怕臭,向贫下中农学习…没有草粪臭,哪有稻谷香!”有老师带头,不一会怕脏怕臭的情绪就被克服,师生们都跟社员们一样,撒起草粪来,撒着,撒着,有女同学(名字忘了)惊叫了起来,这女同学跳上田埂,大声呼唤:“哎哟!妈呀!痛!痛!”同学们围看,原来是被蚂蝗叮咬了,男同学用手指掐着蚂蝗往外扯,却越扯蚂蝗越往里钻,女同学恐惧得大哭起来,这时程老师带来一老伯妈(老社员),这老伯妈用手在女同学被蚂蝗叮咬的小腿肚部位,不停的拍打抖动,蚂蝗就自行退出来了。待这女同学安静下来,同学们才仔细检查,几乎所有的师生都被蚂蝗叮咬,有同学的小腿被蚂蝗叮咬,蚂蝗吸血饱胀后,缩成一团,自行掉落,还留下汨汨流血的伤口。
我记得我当时分在斑竹园的人家姓娄,男主人叫娄新华,女主人叫张XX,是一对刚成家不久新婚夫妇,当时我已能肩挑一百三、四拾斤,上工时我与娄新华挑粪到田里,一个早上我俩就能挑一两千斤到田坝,为他家赚工分达60多分,故很受他家人喜欢,每晚回到家,女主人总做一个好菜给我们吃,那个好菜就是辣面炒肥腊肉,在当时,好吃极了。
说是要学习解放军,要做到到哪家,就要让哪家庭院干净,水缸水满,在斑竹园我做到了。我早上起来,他家人都还没起,就到了他家家门口,拿起竹扫杷就打扫卫生,扫完院坝就去挑水,可这次挑水,我碰上杠头了,娄家的那口水缸,是用五块大石板做成,高约1.1米,宽1.2米,长1.6米,(以前农村常见,缸底是一大石板,石板四边凿有条槽,再把四块石板镶入条槽,形成一长方形的石缸)能盛水近2吨,其水井在距他家厨房下方约60米,全是简便的下坡小道,下坡是空桶,满水是上坡,第一天早上,我就挑了十多挑水,可倒在缸里面,还不到三分之一,每天耗水约两挑,第二天我起得更早,连挑了二十多挑,才把水缸挑满。过后,我听到女主人与他人议论:“我家得的那个学生真能干,我来到娄家已两年,我家那口水缸我从没挑水倒满过,他从昨天就抢着挑水,今早把水缸挑满水了,真是个好学生” 。那时,能得到贫下中农社员赞扬,就觉得是又红又专最大的政治名誉。
在斑竹园支农,吃的是大米、包谷杂粮,生活比起在凯口营盘要好得多,但劳动比较艰苦,全是坡坎梯田和山地,上坡下坎走路腿都打紧,印象最深的是被蚂蝗叮、猛子咬,当支农结束,几乎每个同学和老师都有过敏皮疹产生,而那时治皮疹的药,就是程老师和几个女同学带的万金油。
七
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话,却有有线广播小喇叭,广播通知,支农结束,我们斑竹园小分队到大坪(现之大坪镇)公社处坐车回校。
来时,是从斑竹园东南方的一小山冲走来,而大坪公社却在斑竹园的正西方,并说是斑竹园走路到都匀最近的路,社员们指着斑竹园正西方的对面山丫口,说:从那山丫口走出去,就到大坪。
通知要求,11:30必须赶到,在社员家吃过最后一顿早饭,于9点整我们就向大坪出发了。
天有不泽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想到,这次,我们班出事了。这事还不小,是全校唯一的出事事例,程远召老师的腿跌断了。
从斑竹园出来,顺山坡小道,经过大包谷地,走了约20多分钟的山路,就来到通往大坪的山丫口附近,当时山花烂漫,同学们有的采花,有的追蝶,欢乐兴奋,不亦乐乎,程老师不停呼唤:“注意安全,不要走远!”一到大丫口,往下一看,大坪村寨就在山脚下,公路畹蜒,田园缀叠的景像就在眼下,同学们好象是新奇路近,又好象是回家心切,下山简直就象小跑。程老师不断招乎:“小心,别着急,慢慢走” 。
大丫口是一很陡峭的羊肠小道,呈之字形向下面的山脊延伸,由于同学们不听程老师招乎,全都下到了大丫口下缓平的地带,把程老师抛在了后面,我和罗时平、曹玉书、杨永德以及两位女同学看到程老师还没跟上,就停下来等老师,程老师距我们也就二十多米了,正在走出那段陡峭的山路,不想事故发生了,只见程老师突然身往前趋,随后跌了一跤,倒身在地,就大声的呻吟起来,我们几个同学跑上去,急忙去扶程老师,不想,程老师已不能站立,只好顺着坡地,托着脚手把程老师挪到山地稍平的地方,程老师不断呻吟,并对我们说:“赶快向学校报告!就说程老师腿跌断了”我们几个男同学说:“老师,不怕,我们背得动您!”说着,罗时平就去背老师,谁想,把程老师扶起,就看到程老师的右(左)小腿中段翘了起来,程老师大叫:“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一时,动都不能动,个个束手无策,这时,有的同学已下到了半山,我和陈永德大声呼喊:“同学们,程老师负伤了…”同学们又都跑回来,围在程老师身边,不停喊:“程老师!程老师!….”有女同学看着程老师痛苦的样子,还着急得哭了起来,程老师边呻吟边嘱咐:“赶快去向徐老师报告,向校领导报告!”当时,好象是我们班同学陈志平和贾家敬跑下山去报告,我们在山上守着程老师等待。
等了近一个小时,也不见老师们来,我想,应该尽早把程老师抬下山,可程老师那跌断的腿一动,就翘了起来,根本不能动!我突然想起电影里救治骨伤患者需固定方能搬动的情行,就向同学们说:“赶快去找木板!”同学们问:“找木板干什么?”我说:“程老师的腿有木板固定,就可搬动了!”于是我就往山下村寨跑,恰巧跑到距程老师受伤处不到百米地方的松树林,有农民解板剩下的禾边板,我拣了两块较好的就回到程老师身边,我叫罗时平把住陈老师膝盖的大腿处,我拉着踝关节处,就用两块松树禾边板夹住,就叫拿带子来捆绑,当同学们看懂了我的用意,就象晃然大悟一样,纷纷去找带子,然而,却没有带子,这时,有一同学(时间久远了,记不住是谁了)脱下衬衣,三下五除二就把衬衣撕成带子,才把程老师的伤腿固定完成。真是见效,程老师伤腿固定完成,疼痛就减轻了,也不呻吟了,却还惦记同学们去赶车,这时离11:30分开车只剩十多分钟了,程老师嘱咐罗时平、曹玉书、杨永德和我留下,其余人均下山赶车。
直到此时,也没有见校领导方来人,也不知道陈志平与贾家敬报到信没有,程老师受伤处距大坪公社约有一公里,全是在山脊的松林小路穿行,全是下坡路。
经过固定,程老师可以背着走了,但不能剧烈抖动,罗时平个头最大,由他背着程老师,我和曹玉书用手抬着伤腿,杨永德负责开路(有树枝、荆棘拦挡负责拨开),走不到300米,罗时平就大汗淋漓,我接着替换,说来也奇怪,我们四个人都是农村出生,当时都能肩挑一百二三拾斤,程老师体重也不过一百多斤,背起来就是那么沉,走了300多米,我也大汗淋淋了,罗时平又来换上,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我们下到山脚的大坪公社时,已是下午13点过了。同学们已全部坐车走了,就剩下我们五人,加之程老师负伤的惨象,显得有些凄凉。围观来的社员群众和公社领导告诉我们,校领导已知道此事,正派车往这里赶。
热心的社员送来一较大的椅子,我们把程老师扶上椅子坐好,并用木凳把伤脚垫好,就在那里等车,等了近15分钟,才见一辆吉普车开来,一老师(是哪个老师现已记不清楚了)和驾驶员走到程老师身边,直说:“程老师,你受苦了!”程老师激动得哭了起来,当时那情景,连我的眼睛,也饱含着泪水。
我们把程老师抬上车,吉普车后座只有三个坐位,程老师横坐上去,把伤腿顺坐位坐下,就没位子了,曹玉书横坐在坐位边缘扶着程老师,程老师斜躺在他胸前,杨永德仄身坐在坐位前侧用手扶护着老师的伤腿,车子再也坐不下人了。我和罗时平只好徒步走回都匀。
“赶快把程老师送到医院!”是我们当时说的话,车子开走了,当时的公路还是泥巴碎石铺垫的路面,只见公路扬起一阵灰尘,不一会车就不见了。
从大坪到都匀,据说,有三十多里路,这是我从娘肚皮出来,第一次徒步走这么远的路。我和罗时平向老百姓问好路径,就出发了,我们先顺公路向北走,约一个多小时到达老牛昌,再半小时后到达牛昌,在牛昌问:到都匀怎么走,有人告诉从木脑坡走最近,我和罗时平边走边问,来到木脑坡(即现之大龙大道遂道洞口山丫),爬上木脑坡山丫口,就看到了学校的东山和匀城蟒山,不由兴奋不已,路全是山区小道,顺着木脑坡山冲下走,过高基寨子,再到沙子坝(现精神病院,那时根本没有人家),就到了东山脚下,于下午17:30时,到达一中。我和罗时平已饿得不行,急忙去学校食堂打饭,打饭中碰上杨永德,杨永德说,程老师已住院,我们才放心下来。我不是住校生,是杨永德和罗时平共同出的饭票和菜票使我在学校吃了一顿饭,这也好象是两年中,在学校食堂吃的第一顿饭和最后的一顿饭。
那时,可以说我是程老师的得意门生,因程老师教导有方,我的数学成绩在全班最好,每次考试都在全年级的第一、二名,从没拉到第三名,我还记得当时高中部的吕(鲁)皆祥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被刊登,王平校长还叫老师们推荐优秀学生去开会,办活学活用,精而简练的学习班,我就是被程老师推荐去的。
没想到,政治风云突变,先是批判廖沫沙,继而批判蹇伯赞、《三家村杂记》,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从而使我想当数学家的梦,破灭了!从那以后,我与我们班的同学再也没有见到过程远昭及徐仁甫老师。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9046 准媳妇
- 浏览:7884 祖孙情
- 浏览:7386 战将观后感(一)旋风司
- 浏览:6204 《农民工》接龙
- 浏览:5731 “句町”读音辨析
- 浏览:5592 好事近
- 浏览:5116 效率才是第一生产力
- 浏览:4842 生活中的辩证法(随笔)
- 浏览:4686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观后感
- 浏览:3823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