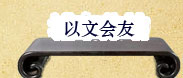老屋 
北方人习惯睡土炕,不习惯睡床。我在十七岁以前,每天晚上都是睡在炕上。直到十七岁那年冬天我去甘肃当兵我才第一次睡在床上。 略懂人事起,我就在三间老屋子里睡觉,那就是我的家。
那房子也许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四面墙找遍了也找不到一块齐整的砖。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明两暗三间低矮的小房子。外屋有一个红漆板柜,上面常年铺一层旧挂历纸,在放上案板,就可以在上面切菜了。柜正对面是一个锅灶,一家人的肚子全指望它呢。所以外间屋实际就是厨房。东西两侧分别是卧室和仓库。我们的卧室摆设极其简单,一桌两椅一柜而已,剩下的大半个屋子都被那一条土炕占了去。土炕不算家具,它是建筑物的一部分。梁思诚先生作《中国建筑史》对中国建筑物有最详尽的论述,但他唯独漏掉了土炕这一节,毕竟广东人不懂这玩意儿。那时候爷爷奶奶都在,每回吃饭的时候,小方桌就摆在炕上,爷爷自然居中而坐,老少三代同桌而食,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妈妈忙着伺候一家老小,总是最后一个才吃。那时候妈妈似乎还很年轻,也很漂亮,脸上没有一条皱纹,满头看不到一根白头发,尽管一家人时常为一日三餐而担忧,但这似乎与漂亮并不矛盾。我小时候最喜欢下雨,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雨伞之类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妈妈必定不同意我去学校,一来如果淋了雨得了感冒,又要花钱看病,她实在心疼钱,在说她也实在心疼她的儿子啊,所以她必定会说“那么大雨,别去了。小孩子哪个不怕念书啊,所以这时候我会很高兴,甚至连肚子都不那么饿了。
我们的锅时常干净的像个体面的小寡妇,那年月,爷爷喜欢靠在墙根下抽烟带锅,一阵阵烟雾随风散去,暖暖的阳光照着他懒洋洋的身子。奶奶时常骂他老不死,爷爷耳朵背,听不清老太太说什么,只会咪着眼一个劲笑。奶奶是个小脚女人,自然是不方便下地干活,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那双脚,那是一双畸形的脚。奶奶坐在炕上缝补丁,我就摸她那双脚,挠她脚心,奶奶乐得连皱纹都舒展开了。
睡过土炕的人都知道,冬天睡土炕必须要烧大量的柴禾才会暖和,如果没柴烧那土炕晚上睡在上面就会冰凉,所以为了解决柴的问题妈妈不得不大冬天四处找柴火,妈妈背着个大筐手里拿把耙子,一筐筐的往家里背,枯树叶,干树枝,都堆在墙根底下,堆得高高的,像小山似的。记得 那年冬天雪下的特别早,大雪把什么都埋住了,妈妈一连几天找不到柴禾,那天晚上风特别大,我们一家睡在冰冷的炕上,妈妈把我搂的紧紧的,而她自己却一直打哆嗦,好容易熬到了天亮,而东屋里爷爷早已咽了气。那天下着大雪爷爷出了殡,奶奶哭得死去活来,那一天之后奶奶没在笑过,常自己坐在炕上两眼望着墙出神,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奶奶一有空就坐在炕上好像很累很累,果然不到一个月老太太就在也起不来了,到最后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奶奶快不行了,嘴里一直念叨个不停,谁也听不清说得什么,父亲把耳朵贴到奶奶嘴边才听明白奶奶其实只是在重复说着三个字,在仔细听才听清楚原来那三个字就是爷爷的名字。就这样老太太念着老头子的名字死在炕上了。这一天是爷爷死后的第二十九天。曲终人散,花落春归,,昔日堕水成离,而今化泥方聚,她们在化作泥土的一瞬间,相聚在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必定是一个嘴里骂着老不死,一个叼着旱烟傻笑,也可能是一个添柴,一个加水,就那样快快乐乐的生活着。那一年冬天,我看到一对逃难的夫妻带着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从我家门前走过,他们衣衫单薄,举步维艰,男人紧紧的牵着女人的手,一路坚定的向前走去,他们身后的雪地上,留下几串长长的脚印,看着他们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风雪之中,那一刻我看到一幅凄美动人的流民图。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与子偕老,什么叫人间真爱。
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冰雪慢慢融化,花儿悄然绽放,邻家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洋槐,槐花开放的时节,整棵树都是白的,微风吹起,总有许多槐花随风飘过我们这边来,地上像下过雪一样美丽极了。在一个芳草碧连天的日子,姐姐穿上红红的嫁衣,在一片唢呐声中嫁为人妇,有生以来,姐姐最好看的一次就是那一天。在后来,我家盖新房了,我坐在草垛上眼睁睁的看着我家三间老屋被工人推到了。在老屋轰然倒下的一瞬间,有种说不出的痛。谁不喜欢住漂亮的新房子呢,那是多么叫人高兴的事啊,但是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总是让大人们琢磨不透。那个曾经为我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遮风挡雨的老屋永远的消失了,那里有我的爷爷,有我的奶奶,还有我写满纯真的童年。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9043 准媳妇
- 浏览:7881 祖孙情
- 浏览:7385 战将观后感(一)旋风司
- 浏览:6202 《农民工》接龙
- 浏览:5723 “句町”读音辨析
- 浏览:5590 好事近
- 浏览:5114 效率才是第一生产力
- 浏览:4839 生活中的辩证法(随笔)
- 浏览:4685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观后感
- 浏览:3821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