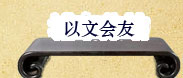内容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25篇:在4700公尺的高原用手摇钻探机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25篇:在4700公尺的高原用手摇钻探机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二十五篇:在4700公尺的高原用手摇钻探机
只要一提到湖,特别是西藏高原上那些海拔或高或低,面积或大或小的湖泊,所有的影视画面上几乎都能够看到:瓦蓝瓦蓝的天空,白亮白亮的浮云,刺破蓝天的雪山,明媚绚丽的草原。再细看那湖:水波荡漾,一碧万顷;鱼游水底,鸥翔湖面……就在此时,你的耳边一定还会响起那令人荡气回肠的高原歌曲,真正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心驰神往的画面呀!这几十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无数次走进过这样的画面。直到今天,我虽然身不由己,洒泪惜别了最亲最爱的高原,但是每当我在影视上看到那湖光山色的画面,听到那石破天惊的歌声,一股暖流就会立刻传遍全身,我也就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辽阔的羌塘高原也有那么一些湖(全都是咸水湖),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就拿1958年我们的工作区域班戈湖的二湖来说,湖面全是高低不平的硭硝壳;湖岸是褐黄色的乱石滩;湖边难见到一棵草。一场大风刮过来,昏天暗地灰茫茫;一场大雨泼下来,湖里立即变成了烂泥塘。加上4700米的海拔高程,年平均零下三、四度的气温。来自江苏的地质员小万无可奈何地长长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轻轻地摇着头,再运用他在地质学校学得的知识,给班戈湖定了个“性”:“这也能算是一个湖吗?还不如将约旦河谷南部那个死海的名字借给它,干脆就叫它“半个(班戈)死湖”,那才是名副其实哩。”
但这些还算不上真正的困难。要说难,要说苦,我首先还是想说说那些钻工师傅。先就从他们那非同寻常的经历说起吧。当年班戈湖地质队的那些钻工师傅,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枪林弹雨,不少人还负过伤。在五十多年前,人们就尊称他们为“老革命”。
再说说他们使用的钻探机。1958年班戈湖地质队使用的是两台50米手摇钻机。论“辈分”,它应该算得上是钻机家族的老祖宗;但论个头,它可又是钻机家族里的孙子辈了。手摇钻机的结构也很简单:钻机立轴两边各有一个大转轮,每只转轮上连着一根铁摇柄;三根长钢管连成一个三角架,升降钻具的滑轮就吊在那架子顶上。钻进时,班长掌握给进把,四个钻工分立在两旁,握住摇柄使劲摇。你摇一摇,钻机立轴就卡住钻杆转一转。你用的力气大一点,它的进尺就快一点;你使的劲小了,它进尺也就慢了;你累了,摇不动了,它也就干脆停下来不转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曾编有一本《人在高原》的书,认为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无法定居,并以此为依据,将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称之为“生命禁区”。1978年我调到地热地质大队工作,在大队使用的柴油机技术资料上就看到: 6250型柴油机,在气温20摄氏度、相对湿度50%,海拔高度4000米时,功率比海平面下降了47%。这也就让我又想起了当年的班戈湖。我想,柴油机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铁疙瘩,它“喝”的是柴油,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那么一个铁疙瘩竟然也会患“高山反应”病,功率较海平面下降了将近一半。那么当年班戈湖的那些“老革命”钻工师傅呢?他们每天就是吃着半生不熟的米饭和黏糊糊的馒头,喝着味道怪怪的水,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将自己的“血肉之躯”当做柴油机,他们的“功率”,又应该用什么“公式”来计算呢?
这还只是说的海拔高度和缺氧,这是班戈湖的地理“常数”,在它面前,钻探工与从事其他工种的人们遇到的困难是1:1,彼此彼此。但是班戈湖那可怕的气候“变数”,却给钻工师傅带来了更多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前面说了,50米手摇钻机十分简陋,没有钻塔,完全是露天作业。钻探施工时人们几乎无一日不在经受着烈日、寒风、暴雨、冰雹的“考验”。常常是:火辣辣的太阳像是一只大炭火炉,卷起滚滚烈焰,灼人的热浪充塞着整个空间,使人喘不过气来,只感到脸上火烤般地烫,眼也睁不开,人都成了一只只蔫巴巴的烤土豆。那原本就稀薄的氧气,经这“炭火”一“烤”,变得更加稀薄,人们呼吸困难,窒息般地痛苦,除了吱吱响着的钻探机,谁也不愿意开口多说一句话,空气好像也凝固了。这时候,唯有那话篓子赵师傅竟然还是管不住自己那一张嘴,偶尔还会费劲地、断断续续地发表着议论:“古,古往今来,都,都说那,英雄难过美,美人,关。依我看,现如今,只要,只要多给我一口氧气,就是那,貂禅再生,站到了,我的面前,我,我也发誓,绝不会看她一眼!”也只有此时此地,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平日里谁也没有意识到的氧气,在班戈湖,却成了一件多么珍贵,又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宝贝啊。
我自从当了计划统计员,就经常到钻机去跟班劳动。一天我到二号钻机去跟班,开始时我的心情也跟蓝蓝的天空一样地好。就这样子钻进了几个回次。我手摇动着钻机摇柄,情不自禁地哼出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可还没等那下半句的马儿“跑”起来,很远很远的天边边上,悄然浮起了几缕淡淡的云彩,一会儿工夫,那原本蓝得发黑的天穹深处,猛地响起一阵干巴巴的炸雷:“格,隆隆隆……”接着狂风突起,卷天席地地扑了过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天地立刻连成了一片。狂风嘶叫着,翻滚着,凶暴得像要将人撕成碎片。我抬头看看天,只见乌云压顶,让你感到天好像马上就会塌下来。突然,利剑般的一道闪电,一下子将那乌黑的天空劈成了两半,天地变得一片惨白,紧接着一串沉雷,大地颤抖。沉雷刚过,天也就像是被谁戳开了一个大口子,哗——地泼下来一阵揭地掀天的大雨。李班长二话没说,一把将钻探班报表卷起塞进了自己的怀里,跟班地质员急忙用自己的雨衣盖住了岩心箱(因为硼矿岩心经猛雨一浇就会被冲坏,直接影响到岩心采取率)。成千上万吨的雨水,不停地倾泻下来,我只觉得空中的雨水竖着在往地上倒,地上的积水横着在向四处流。我们刚刚被烈日烘烤出了一身臭汗,连胶鞋里都灌满了汗水,可这会儿被冰冷冰冷的雨水一浇,又立即变成了一只只冻得上下牙齿直打战战,掉到了泥汤里的鸡。虽说大家都穿上了雨衣(除了跟班地质员),但在那猛烈的雨夹雹的袭击下,全身早就被浇得没有了一根干丝,人们还不敢让钻机停下来,因为钻机停止转动,时间一长,钻具就有被湖里的烂泥巴紧紧卡住的危险。你只得一边咬紧牙关抵御着风雨的袭击,一边继续使劲摇动钻机,捱到风雨过后,再靠自己那可怜的一点点体温去“烘烤”湿透了的衣裤。
但有的时候,开始时也会叭哒叭哒地掉下来几滴黄豆大小的雨滴或冰雹,就像是来给人们打招呼:“喂,我来了哟。”一刹那,大雨就是瓢泼,甚至倾盆了。这班戈湖的雨,大多数还夹着雹。往往是核桃般大小的冰雹夹着雨水,不是“下”,而是劈头盖脑地砸下来,甚至是直接捣了下来。有的时候,也是光响雷,刮狂风,却不下雨。但那来去无常的狂风同样吓人。大风一来,像是有千万头野牦牛和狗熊扯着嗓子在嚎叫,在狂奔,整个天地间充满了恐怖的吼声。风裹着刺鼻的芒硝粉铺天盖地、黑地昏天地横扫过来,吞没了一切,四周灰茫茫一片,人像掉进了浑水中,用不了几分钟,你满嘴巴、满鼻孔、满耳朵,甚至是全身的每一条皱纹,每一个毛孔统统塞满了芒硝灰。可是你的手还要紧紧地抓住钻机摇柄,以防自己也被狂风刮走。一次,人称黄大头的一号钻机的黄师傅,就真的被风刮走了,害得赵队长派人出去找了一整天,最后在湖南边的小山沟里才将晕倒在地的他找到。回来后,队长赶紧扶他在行军床上躺下,再递上一杯热开水,随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三班长(过去黄师傅在朝鲜时是班长),我记得那次阵地遭轰炸,老美的重磅炸弹也没能把你炸迷糊,现如今,一阵风就将你弄成了这模样?”大头难过地回答道:“老营长,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天还真的迷糊了……”直到后来,我才从一本介绍高原的书上知道,在高度缺氧的情况下,人们常常会发生错觉,甚至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来。几个月下来,不少人得了关节炎、气管炎。
再说说人们的生活,听说连敬爱的周总理都多次过问班戈湖的粮食供应。班戈湖从没缺少过大米白面,可就是做不出熟饭来。煮大米饭时,炊事员将灶火烧得旺旺的,还特意延长了煮饭的时间,甚至将贴着锅子的那一层“锅巴”都烧得冒了烟,可锅里依旧是夹生饭!还有那黏糊糊的馒头,任凭你变着法子“蒸”,一个个馒头都像现如今那“502”万能胶,你的手一碰上它,一层黏糊糊的面糊糊就会紧紧粘到手上来,不用水洗根本弄不干净。这万能胶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们粘信封从来也不需要胶水,它比胶水还牢靠。再有就是下面条,一大锅水烧得翻滚起来了,任凭你再加大火力,延长时间,那水温也就是八十来度。炊事员无奈,也就只能将面条下到锅里去,很快就变成了一锅面糊糊。开始时,有人埋怨炊事员连面条都不会下,还当什么炊事员?过了不久,人们才发觉还真是错怪了好人,真正的原因是班戈湖的海拔太高了,水的沸点低。但那时候,“高压锅”在班戈湖连名词都没有人听说过。人们也就只好将就吃着那半生不熟的夹生“饭”。结果是肚子胀得难受,不断地放屁。平时就爱开玩笑的地质员大老李问大家:“同志们,你们知道肚子为什么会发胀吗?”见没有人回答他,他又自问自答道:“这是半成品的大米正在各位的肚子里进行再加工。至于放屁嘛,那是因为肚子加工机也要排气哟。”逗得大家一阵苦笑。更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用汽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的高成本“生活用水”,喝下去味道也是怪怪的,肚子不是胀就是泻。就连偶尔用它洗一把脸,手上脸上都会有抹上了一层油的感觉。我觉得那水里就是有油。至于其他的副食品,特别是新鲜蔬菜,就全要靠拉运器材的汽车偶尔从西宁稍一点上来了。可就是捎来的那一点点菜,光在路上就得耽搁十来天,新鲜菜早就成了‘脱水菜’;再加上要穿越可可西里、唐古拉山一道又一道的 “冰冻封锁线”,等运来班戈湖,少得可怜的那一点鲜蔬菜早就成了冰坨坨。人们成年累月吃着腌萝卜、腌大头菜、煮黄豆,连改善生活时吃的猪肉也是咸的。
一天傍晚,人们收工回到三湖边临时搭起的帐篷,炊事员从基地送来了晚饭。大家正准备吃饭,一阵狂风裹着大雨突然袭来,眼看帐篷就要被狂风卷走了,人们赶紧丢下饭碗,出去加固绳索。大风过后,回到帐篷,锅里碗里统统都盖上了一层泥沙。再回基地去做饭已经来不及,大家也就只好在碗里倒上一点水,用筷子搅一搅,让泥沙沉到饭的下面去,‘咯吱咯吱’吃了一顿“泥夹饭”。
再说人手也严重不足。一次我问赵队长:“队长,地质部人员定额规定,手摇钻每台定员15人,那还是在内地。可我们队只有12人,若是有人生了病怎么办?”赵队长看了我一眼,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又给我讲起了“过去的故事”。他说:“在朝鲜,我们营的高射机枪连被敌特发现了,美国鬼子的轰炸机暴风骤雨般丢下来成吨的炸弹,一眨眼功夫,整整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个人,可还得照样打敌人,守阵地。”好像要验证他的这一句话,几天后,二号钻机的钻工大老刘患感冒真的爬不起来了。赵队长说:“今天预备一组上。”我心想,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队长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看你这“预备一组”从哪里变出来?只见赵队长一声不响,换上工作服,跟上钻工们出发了。原来,队部所有的行政管理干部(包括赵队长自己和另一位“年轻的老革命”机要员老张),早就被他编成了“预备队”。我想,到底是打过日本鬼子又打过美国佬的独立营长,处理事情就是不同凡响。这种“预备制”一直保留到1960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我队完成了1958年的野外地质工作任务。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发表评论


分享本站
- 作品排行榜
- 浏览:9043 准媳妇
- 浏览:7881 祖孙情
- 浏览:7385 战将观后感(一)旋风司
- 浏览:6202 《农民工》接龙
- 浏览:5723 “句町”读音辨析
- 浏览:5590 好事近
- 浏览:5114 效率才是第一生产力
- 浏览:4839 生活中的辩证法(随笔)
- 浏览:4685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观后感
- 浏览:3821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