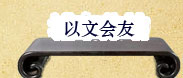少时,初学英语,纯属偶然。1970年代初期至中期,华北农机考察团(也称“北京农机学院考察团”)在沙河县文化馆住着若干人,说是考察,其实很多成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其中一位叫柳克令的先生,五十多岁,颇有学者和绅士风度,与家父交好----家父当时也因家庭历史问题(我祖父清华大学辍学后曾在民国沙河县政府供职)被下放回到老家改造,俩人由此结识,相处融洽。 一次,我去柳先生居室小坐,他在外边忙碌,我闲着无事就转看他室内几个书橱里的书籍,发现里边全是拼音字母构成的课文,按照汉语拼不出意思,很好奇和纳闷。柳先生进屋看见我按照汉语拼读,就解释说这是英语书。我忽然想起电影里的外国人叽哩哇啦说得难懂的话,就萌发拜他学习英语的念头,说了出来,柳先生爽快答应。当时,全国少数地方开设俄语教学,极个别地方因需要而教授英语,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落后的地区没有开设英语课程。我们邢台这里的沙河中学开设俄语课程(后来才改英语)。所以,也无处搜寻英语教材。柳先生手中没有现成的适合启蒙的外语书籍,就委托亲友在外地寻找,最终搞来一本好像是由广东等四省合编的三十二开本的薄教材,一套好像是六册,这就是我的英语启蒙教材和英语学习的初始。
柳先生教授我英语,从字母、音标到词句,如同家长教孩子,非常认真耐心。很多时候,一个音标或长单词不好学,他就一直领读、示范、纠正,直到我学会读正确为止。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简易英语读物,更遑论英语词典和语法书籍了。仅仅这一套简易的初级启蒙教材,柳先生就一边教我学习课本,一边训练我日常口语。担任北京农机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教务主任的柳先生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在美国留过学,所以我的口语自然带有些许的美国味道---及至多年后我参加美国口语培训的时候,很多人感到纳闷呢。为了提高我学习能力,柳先生委托女儿从北京给买了一本郑易里主编、上世纪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華大辭典》教我查阅词典,扩充词汇,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外语学习工具书,记得当初是小开本,硬壳封皮,里边的汉字都是繁体字,我很多不认识,只好硬着头皮一边学习查阅英文,一边跟着柳先生认读繁体字,这本词典一直陪伴我,直到读中学开设英语课程时买了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英華大辭典》那时候已经被我翻阅得破烂不堪,临近解体了。柳先生教了我两年多,为我的英语学习奠定了扎实良好的基础,待到冤案昭雪,他调回了北京。之后,我们曾经几次通信,因地址变迁,最终失联。考察团其他成员也在七十年代末获得平反后陆续调走,个别人在八十年代初调走。
我初学英语时,恰逢英语书籍奇缺的年代,没有语法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薄冰、赵德鑫编著的《简明英语语法手册》才算是有了可供查阅语法的书籍。但很快我就感觉这书太简单,讲得浅显,不够细深,不能解决我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更难以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恰好,后来从一位自称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解放后在附近一所中学看门的老人处获得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英文版《简明英文法典》,我如获至宝,但一看就傻眼了,因为里面全是英文,很多术语根本看不懂,只好经常请教我的外语业师,以及查阅词典才能勉强读下来。
及至攻读大学英语教材时候,依然只有一套北京外语学院主编的《College English》教材系列的几册课本、一本语法书和之前的《新英汉词典》陪伴我整个学段,课外阅读资料也是极为有限,十分匮乏。
我参加工作后,有段时间没有从事外语,做办公室工作等杂务,远离外语,内心还恋恋不舍,有些纠结。当时因为很多地方的外语教师不足或质量不高,我去了某企业学校执教外语,才重新深情而持久地“亲吻”英语。
踏上帆船,学海泛舟,我便下定了遨游外语“太平洋”的决心,为了渴望已久的梦想扬帆远航。
从邢台调走、后任辽宁抚顺财政局长的好友马国明兄得知我去执教外语后,从远方寄赠我一本《牛津髙級英漢雙解詞典》供我教学查用,里边汉字很多也是繁体字,而且字号很小,读起来吃力。这部《牛津髙級英漢雙解詞典》作用重大,陪伴我度过了很久,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差在邯郸购买了一部梁实秋主编的《逺東英漢大辭典》,内中汉语也是繁体字,不过经历了《英華大辭典》和《牛津髙級英漢雙解詞典》洗礼之后,我不再发怵繁体字了。当年在加拿大读研的好友侯伟久兄也写信鼓励,说我从事外语才是回归正道,利于我的发挥和发展。
然而,执鞭不久,我发现外语的求学和任教有着天壤之别。求学时候,比较简单,“听说读写译”这些项目能基本完成要求即可。阅读资料少,自己一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有限,偶尔遇到难题就可问老师---尽管我的很多疑难,老师的解答不能令我满意。但执教就不同了,经常遇到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有我自己学习中遇到了不明白的,有同行探讨时提出的质疑,有学生课堂提问的难点,反正是千奇百怪,我在学校所学的英语知识根本不足于解释这些问题的十分之一,甚至无法应对。我请教本单位或市内的同行,不知是他们真不懂而解释不清,还是明知而不告诉我这个年轻后生,故意刁难我,反正很多时候,教学中遇到的英语疑难总不能顺利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去图书馆查阅有限的资料,也很少能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对于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我总是百思难得其解,苦恼不已。只好逐一记录在小本子上,随时装在身上,遇有出差机会,我就一头钻进当地图书馆或书店,半天查阅,或鼓足勇气去当地著名大学拜访知名外语学者,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提出问题并质疑。起初,不好意思,日久就习惯了。很多著名外语学者都非常坦诚而朴实,对我这类的年轻后学给予热情详尽的解答和指导,一般不会拒之门外。比如我先后曾经拜访和求教过的北京外语大学薄冰教授、许国璋教授、陈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孟雄教授,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刘道义编审,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室顾问、清华大学外语系《大学英语》主编李相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易代钊教授,上海外语大学章振邦教授,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张正东教授,商务印书馆编审、《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先生,以及在中国大学任教的部分外籍专家等,聆听他们的讲学,日后遇到问题经常通信请教,他们都会逐一认真解答,特别是刘道义女士、薄冰先生、李相崇先生等学识渊博,却虚怀若谷,除了当面指导,还在耄耋之年不时亲自回信,认真解答我日常遇到的疑惑,并赠送很多他们主编的外语书籍,对我的外语教学和个人进步给予了莫大的帮助。可以说,我遇到这些前辈是我的福气。
随着学习的日渐深入,我越发感觉自己学识的欠缺,发现自己知道的太少了。我开始在邮局订阅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类英语报刊。起初,不懂得挑选哪些报刊适合我教学和自修,就盲目根据邮局的报刊订阅目录随意查找,一发现是英语类的,就直接圈住订阅,结果在初始几年的每年十一月份,仅订购杂志这一项就花费我当月工资还不够---只有央求邮局的尹师傅先办手续,开了工资再补交,反正我经常在他这儿订阅,熟悉了,他也很喜欢我,就关照允许。遗憾的是,我盲目订阅的很多杂志只有空洞理论,并不真能解决我的教学实际问题。最后,我只好保留经常订阅几种杂志,诸如北师大的《中小学外语教学》,华东师大的《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华中师大的《中小学外语》,大连外院的《英语知识》,上海外院的《英语自学》,清华大学的《大学英语》,商务印书馆的《英语世界》,北京外语大学的《英语学习》,江西出版的《英语辅导》,河南大学的《中学英语园地》,吉林的《英语辅导报》及山西的多种英语报刊(当年山西出版外语读物最多)等。阅读中,每种杂志里相近的内容我都会标注,以方便相互参考。这样一直坚持订阅了十几年,每年的报刊我通读完,都分门别类装订起来。如今我的书橱里还保存着若干早年的外语期刊。
遇有出差的闲暇,别人喜欢去商场或景点,我则经常跑书店转看,或到当地大学拜访外语名家,以求解决随身笔记本记录的疑惑,而每每回来时候总是满满的一大包书,沉甸甸的,还有买书借的外债。
为了方便翻译,仅英汉词典类的,我就购买过《逺東英漢大辭典》、《牛津髙級英漢雙解詞典》、《新英汉词典》、新版《英华大词典》、《汉英大词典》、台湾版《英汉活用词典》等,感觉这些不能满足我对英语词汇的正确理解,于是开始购买英美原版英文词典,如《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等共计十几部中外出版的大中型词典。
我想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精透掌握英语语法,曾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多种语法工具书,先后有薄冰的《高级英语语法》,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章振邦的《新编英语语法》(上下册及新版上下册),四川大学主编的《英语语法词典》,英美人Quirk主编的《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ina. J的《COBUILD ENGLISH USAGE》,CLARK的《A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usage》,Frederic T.Wood的《Usages of prepositions》等二十余套国内外出版的大型语法专著,其它类别的如词法、句法、惯用法、时态语态以及英美国口语、俚语、成语、歇后语词典等各类专著各达十余本,共计约二百本左右。我如饥似渴地全部通读,并在很多地方做出标记或备注,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书的很大部分后来赠给我的若干学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坚持长期收听北京外语大学教授陈琳主编主讲的广播电视教材《英语》的系列讲座,每天早晨准时收听,为了不耽误,父亲给我买了一个马蹄表。我还经常收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节目,提高听力。
九十年代,参加全国学术会或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我充分利用陪着来自英美澳加等多国同行当翻译或座谈的机会,积极与他们广泛交流外语教学和探讨疑难问题,了解他们所在各国的文化习俗,丰富和提高自己。
在我多年的外语学习和执教生涯中,很多人无私地帮助我,诸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道义编审时常指导、解答我的疑难,还在百忙中为我主编的语法工具书审稿和撰写序言,《英语辅导报》总编包天仁先生赠送很多外语资料,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教授费致德先生赠送我他主编的《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北京外语大学著名教授薄冰先生赠我很多他主编的系列语法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许孟雄教授在耄耋之年,时常亲自回信解答我的英语疑难并赠我他老人家编著的《英语疑难研究一千则》,湖南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周定之先生赠送我他编著的《英语动词时态》等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数不清。遇到他们,是我的缘分。他们给予我极大的、无私的帮助,其高尚人品、大家风范和乐意助人精神,是值得我一生珍惜的财富。
那时,我不会搓麻将、不会打扑克,不会喝酒(戒烟后随着社交的需要才慢慢学会的),只会读书,抽烟思考问题。没有学生提问的鞭策,我就“庸人自扰”自设疑问促进自己思考研究,比如“if条件句中为何经常使用现在时态表达将来动作?可否使用将来时,有何区别?”“现在完成时为何不与具体过去时间连用,如果连用会表达什么意思?”“非持续性动词何时可以和时段状语连用,表达什么意思?”为了解决这些疑惑,我或者走势访友,或者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去研读。每当我漫游在读书的海洋里,就仿佛变成了一条渴求知识的鱼,欢乐的汲取着书中的营养。每当我带着很多问题遍查书籍,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而在阅读过程中,忽然发现一点受到启发,从而融会贯通,茅塞顿开,疑惑释然,内心顿觉豁然开朗。那种轻松、兴奋和愉悦是难以形容的,也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随着阅读的深入和视野的拓宽,以及阅历的丰富,我积攒了很多知识,发现很多所谓大师的学术论述不能自圆其说,难以让我信服。我不再迷信权威,开始质疑他们著作中的某些观点。我内心奠定了撰写文章去反驳权威和著书立说的渴望。多年来,我先后在北师大、华东师大、上海外语大学、大连外院、人教社等多处出版的高档学术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先后参与编辑多部学术著作,部分论述添补了传统理论的空白,曾被引用和获得多种省级以上的学术成果奖。陕西师大、内蒙古师大 、英语辅导报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外语教育报刊给我开设过教材辅导系列专栏。为了更好地撰写外语文章,我曾经与国内外知名学者交流----广泛的阅读使我有了这种底气。在与他们的交流探讨中,很多人的渊博学识、高尚人格和勤奋认真,让我深受感动,获益匪浅,一部分专家和我成为了朋友。
此间,我执教过中学英语,也执教过大学英语;既在多个学堂执鞭,也曾设坛授学,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就读各地重点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也指导和扶持了若干年轻教师,成为邢台教育界的骨干;还曾主持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应邀参加过许多学术会议,担任过多种外语活动的评委,也被授予过多种荣誉。
我当年的老上司、人生恩师、国务院煤炭专家、邢台矿务局原总工程师郭励生先生曾经教育我,社会是多变的,一个人的岗位也可能发生多变,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自己的专业技能精湛而不丢弃,你就永远有谋生的资本。正是在郭老这种思想的熏陶和勉励下, 即使做教学管理的时候,我也不曾放弃外语教学和研究----这是我谋生的衣钵。
由于我自认为在求学期间获得的外语知识毕竟有限,而且非常简易,很难满足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而更多的英语知识和技能是在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获取和历练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我的外语都是自修的。但我感谢在我坎坷自学路上遇到的每位给我支持、搀扶我进步的贵人----很多,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我数不清。
我多年的英语学海和执教生涯就这般曲折而丰富地一路走来,英语给我的人生增添了无限精彩,前辈们为我的进步插上翼翅助我腾飞,我感谢英语,感恩前辈。如今,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开了三尺讲台,从事一些资料事宜,但每每回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英语求学路,就感慨万千,感悟良多,于是信笔记之,聊以纪念和慰藉。